|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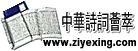 |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 |
|
文/朱光宝 海阔中文网网站整理收录·仅供参考
上编·诗体流变
第一章 诗体之论
第一节 诸家论体
谈到诗体流变,首先要探讨何谓“体”。
“体”的本义是指人的身体。《说文》解释:“体,总十二属也。”意思是说“体”是身体的十二个部分的总称。把“体”运用于文学批评,恐怕与中国古人近取诸身、以类取譬的思维习惯有关。
关于中国古代“体”之内涵,学界看法并不一致。
罗根泽在其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中国所谓文体,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体派之体,指文学的作风(Style)而言,如元和体、西昆体、李长吉体、李义山体……皆是也。一是体类之体,指文学的类别(Literarykinds)而言,如诗体、赋体、论体、序体……皆是也。”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也就是说,在古人所说的“体”中,既有指风格的“体”,又有指体裁的“体”。而在讲风格的所谓的“体”中,也包含了以风格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学流派。
徐复观认为,文体之“体”是指形体,中国古代的“文体”即是他所说的“艺术的形相性”。它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体裁”之体,或称为“体制”,是由语言文字的多少长短所排列而成的形相,是人们容易把握的。如诗的四言体、五言体、七言体、杂言体、今体、古体,乃至赋中有大赋、小赋,有散文,有骈文等是。二是“体要”之体。三是“体貌”之体。“若以体貌之体是以感情为主,则体要之体是以事义为主。若以体貌之体是来自文学的艺术性,则体要之体是出自文学的实用性。若以体貌之体是通过声采以形成其形相,则体要之体是通过法则以形成其形相。”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收入《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这就是说,“体要”之体规定的是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而“体貌”之体是文章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体要”之体和“体貌”之体是高次元的形体。这三者的关系是,“体要”之体和“体貌”之体必须以“体裁”之体为底基,而“体裁”之体只有向“体要”之体和“体貌”之体升华才有文体的艺术性,否则只是一堆文字的排列。
童庆炳先生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的第一章中讨论中国古代文体概念的含义时,他认为,文体是作为系统呈现出来的,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体”、“文体”的含义很丰富,起码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层次:体裁的规范、语体的创造和风格的追求。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从以上的观点看,这些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古代文论所称“体”、“文体”的含义是丰富的,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与内容相对的形式问题,但是,对中国古代“文体”的具体含义的认识却莫衷一是。
第二节 文体始辨
“体”在古代文论中时常出现。用“体”最早的恐怕是扬雄的《法言·问神》:“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这里讲到书有“体”。由建安而魏晋,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文学观念自觉之后,文人“体”的意识就更为鲜明。在理论上开始论说文体分类,首功应属于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将当时八种常用文体及其特征明确开列,把文体一分为八,归纳为四科,用“雅”、“理”、“实”、“丽”来概括各体的体貌特征。虽然用语十分简省,只取一字,却相当精确。曹丕用四个字概括了四种文体的体貌特征,第一次区分了文体,这在文章史上是首创。《典论·论文》区分文体,是以文体的体貌为依据,虽然不涉及各种文体具体的语体特征,但文体的体貌之显现毕竟是通过语言等因素形成的。例如奏议宜雅,雅就要求语言不能太浅俗,语气要庄重,体式要符合规范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曹丕《典论·论文》已接触到体与风格问题。考察陆厥《与沈约书》有云:“自魏文典论,深以清浊为言;刘祯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刘祯奏书原文已不传,详情不可得而知。《文心雕龙·定势》提到:“刘祯云: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这句话应当是刘祯奏书中语。“文之体指实强弱”一句,当有脱误。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认为当作“文之体势,实有强弱”。无论如何,刘祯所谓的体势,当指文章体貌,犹如《文心雕龙》的《体性》《定势》两篇中所谓体势那样。可见曹魏时代已经出现了用“体”字指文章体貌、风格的现象。
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李善注释“体有万殊”句说:“文章之体,有订变之殊。”又释“其为体也屡迁”句说:“文非一则,故曰屡迁。”陆机说文体千变万化,它随着被描写事物的不同情状而经常变化。显然,这里的体不可能是指诗、赋、碑、诔等的体,而是指奢、当、隘、旷、绮靡、浏亮等等多种多样的体貌了。傅玄《连珠序》中论连珠体云:“其文体,辞丽而旨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卷四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傅玄这里是说连珠这种文体的语言风格是“辞丽旨约”,表达的方式是“假喻以达旨”,可见傅玄所说的“文体”内涵包括了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
南朝时代,文学创作方面的拟古风气颇为流行,有的还直接在题目中标明学某某体。如鲍照《学刘公幹体》诗五首,《学陶彭泽体》诗一首,分别学习刘祯、陶潜诗的体貌、风格。沈约还有“文体三变”之论:“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宋书·谢灵运传论》)此说专论历代诗赋的发展,它所谓“文体三变”的体,当然不是指体裁有什么不同,而是指“巧为形似”、“长于情理”、“以气质为体”三种不同的体貌、风格。以气质为体,就是在作品体貌上注意气骨(即风骨)。司马相如的辞赋多铺张的描写,长于刻画事物形状;班彪、班固父子的辞赋,长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抒情说理;曹植、王粲的诗赋是建安文学的代表,富有风骨。沈约的这段评论是相当中肯的,可以充分看到体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作家或者一群作家创作风格的主要特色,这种特色在文学史上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支配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风貌。
从上述引文可见,体指作品的体貌、风格,其所指对象则又有区别,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指文体风格,即不同体裁、样式的作品有不同的体貌风格。《典论·论文》《文赋》分别指出八种、十种文章体裁的作品体貌不同,都是指文体风格。二是指作家风格,即不同作家所呈现的独特体貌。《文赋》中“夸目者尚奢”四句,已经接触到这一问题。《宋书·谢灵运传论》指出司马相如、班彪父子、曹植、王粲作品的不同体貌,说得就更鲜明了。三是指时代风格,即某一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风格特色。这种时代风格常常为一二大作家所开创,其后许多文人闻风响应,因而形成一个时期的创作风尚。《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明司马相如、班彪父子分别对西汉、东汉的辞赋风貌,产生过巨大影响。至于建安风骨,虽不是曹植王粲所开创,但他们两人则代表了建安文学的高峰。所以“形似之言”等特色,也是西汉、东汉、汉末建安三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风貌。
总结前代文论而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对文章的体貌也有颇为细致系统的论述。它对文体风格、作家风格、时代风格三者都有涉及。
先说文体风格。《定势》篇对文体风格作了综合性的论述,其中云:“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该文把二十来种文体归纳成为六类(《典论·论文》概括为四科),指出它们具有不同的风格特色,立论较《典论·论文》《文赋》更为细致全面。《定势》的势,实际上指文章体貌;因为篇中的体指体裁,故用势字指体貌,以免混淆。自《明诗》至《书记》的二十篇各体文章论,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指陈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把它们称为体、大体、体制、要、大要、纲领之要等等。体、大体等是着重就其风格体制特色而言,要、大要等则着重就其规格要求而言。如《诔碑》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又如《祝盟》云:“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可见《明诗》以下二十篇的“敷理以举统”一项,分别对各体文章的体貌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而《定势》则是对多种文体风格作了概括的综合论述。
次说作家风格。《体性》一篇专门论述文章体貌和作家才性的关系。它把文章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八体中两两相对。“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持论比较周密。又指出文章的体貌,决定于作家的才气和学习,对文章风格和作家个性、修养的关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篇中还列举了贾谊、司马相如以至潘岳、陆机等十二位大作家,指出他们由于才气不同,因而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此外,《诠赋》《才略》等篇,对历代著名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都有所指陈,只是没有运用“体”字。
再说时代风格。《明诗》《时序》两篇有较多论述,有的分析得很中肯精辟,《时序》更对时代背景与文学关系做出了深刻的论述。两篇中虽然直接运用“体”字处很少,但也偶见一二。如《明诗》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又如《时序》云:“正始余风,篇体轻淡。”篇制、篇体均指文章的体貌。这是说曹魏正始时代和东晋文学受到玄风影响,因而显示出轻淡的风貌。
《文心雕龙》一书,对“文体”、“体”等词的运用,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体”内涵认识的程度。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中说:“《文心雕龙》中作为专门术语用之‘体’,有三方面之意义,其一为体类之体,即所谓体裁;其二为‘体要’或‘体貌’之体,‘体要’有时又称‘大体’、‘大要’,指对于某种文体之规格要求;‘体貌’之体,则指对于某种文体之风格要求,而在本篇中‘体性’之体,亦属体貌之类,但指个人风格。”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文心雕龙·附会》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几句话意味着文章的体制是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的综合表现,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表现。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文心雕龙》对“文体”内涵的认识是很全面而深入的。
钟嵘在《诗品》中也非常重视体。他在评论许多诗人时,经常注意揭示他们的风格特色,在这方面发表了诸多精辟的见解,成为《诗品》的主要构成部分。他常常指出某家之诗源出某家,也是根据对各家诗歌体貌进行分析和比较而得出的论断。举数例如下:
(评张协) 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
(评谢灵运) 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张协)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
(评魏文帝) 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
(评张华) 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
钟嵘所谓体指诗歌的体貌、风格,如张协的华净,张华的华艳,都是。又如张协诗“巧构形似之言”,谢灵运诗也“尚巧似”,故称谢诗“杂有景阳之体”,这就更明显地从体貌上指出其源流继承关系了。从上引两例言,钟嵘的意思是说:张协诗的体貌是学习王粲作品而来;谢灵运诗的体貌,主要渊源于曹植,又兼受张协影响。《诗品》中有不少地方指出某家源出某家时,不直接运用体字,但实际也是独立从体来论说。如评阮籍云:“其源出《小雅》,无雕虫之巧。”阮籍诗直抒胸臆,质朴不假雕饰,风格与《诗经》的《小雅》相近,故说“其源出《小雅》”。可见《诗品》论前后诗人的源流继承关系,都是就其体貌而言。话如果说得详细一些,就是某家之体出于某家之体,有时还兼受别家之体的影响。钟嵘在探讨前后诗人源流关系时的意见,未必都中肯,且时有简单化的缺点;但这些意见不是凭空发议论,而是根据对前后许多诗人的大量作品进行分析比较而得来的。上文说过,南朝文人创作拟古风气流行。既然在创作上重视学习模拟古代的名家名作,那么,在评论上着重探讨后代作者的作品体貌,主要接受前代哪些人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了。钟嵘在《诗品》中根据对各个诗人作品体貌的分析和比较,把诗歌分为源出《国风》、源出《小雅》、源出《楚辞》三系。《国风》一系中又分两支:古诗、刘祯等为一支,曹植为一支。《楚辞》系又分三支:班姬一支,李陵一支,魏文一支。这种分析论断未必完全妥当,但钟嵘根据体的分析比较来系统探讨历代五言诗的发展流派,是古代文论中的一个创举,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把南齐时代文章(主要为诗赋)分为三体,其文云: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至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其中第一、第三两体,分别为刘宋谢灵运、鲍照所开创;第二体导源于魏晋的傅咸、应璩,但此体喜欢“缉事比类”,大量用典,其近源实出颜延之、谢庄,此点参照钟嵘《诗品序》便可明白。刘宋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是三大诗人,对宋、齐、梁三代诗歌,影响颇为巨大。《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说的三体,实际上就是这三大诗人所创立、提倡而形成的。三体不但标志着三家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在后世形成流派。《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云:晔“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又《梁书·伏挺传》载,伏挺“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从这类记载,不但可以看出谢灵运诗歌在南朝影响之大,而且可以看出当时作诗已流行以某一著名作家名加上“体”字来命名的习惯了。结合上文提到的鲍照《学刘公幹体》、江淹《杂体诗》等例子,更可以明了当时的这种风气。
除以作家名体外,当时还有以时代名体的现象。如《南齐书·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可见这种以时代名体的现象在齐梁时代也流行了。不过,永明体偏重声律,与泛指风格的“体”含义稍有区别。
梁代风行宫体诗,其倡导者是萧纲、徐摛。《梁书·简文帝纪》云:“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又《梁书·徐摛传》云:“属文好为新交,不拘旧体……转(太子)家令,兼掌书记,寻带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宫体诗的风格特征是轻艳,内容题材多述闺房之事。故《隋书·经籍志》称:“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当然,这段话有所夸大,实际萧纲、徐摛、庾肩吾等人的一部分诗篇,内容并不全是流连于闺闱衽席之间。
风格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综合表现,因此风格与内容题材有紧密联系。如陶彭泽体多言田园隐居,谢康乐体多述遨游山水,就是典型的例子。江淹《杂体诗》所拟作家名下加两字注明内容题材,如“潘黄门(岳)悼亡”、“陶征君(潜)田居”、“谢临川(灵运)游山”、“鲍参军(照)戎行”等,更可见出二者的关系。但一个作家的作品,其题材毕竟比较广泛,除特长某种题材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题材。如鲍照诗除长于写从军外,还有不少其他题材。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是植根于多种内容题材上的,除主要或突出的题材外,还有其他题材。对宫体诗的内容题材,似乎也应作这样的理解。宫体诗的特征是轻艳,就体貌风格而言,符合于南朝文人运用体字的习惯。至于描写闺闱衽席的内容,只是宫体诗题材的突出方面,不是其全部。萧纲、徐摛等人的一部分诗篇,初唐诗人的一部分诗篇,其内容并不描写闺闱衽席,但其体貌风格轻艳或比较轻艳,因而都被称为宫体诗。
从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到,自魏晋至南朝,含义为体貌、风格的体这一概念,其内涵已经相当丰富和完备。就指陈对象而言,有文体、作家、时代、流派等区别;就专门术语来说,则有以作家命名的“刘公幹体”、“谢灵运体”等,有以时代命名的“永明体”(此体兼有流派性质),有以流派命名的“宫体”等等。唐宋以来,文论言及风格之体,大致不出此范围。
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有《论体》一段,据王利器先生《文镜秘府论校注》考证,系出自隋代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一书。文有云:
凡制作之士,祖述多门,人心不同,文体各异。较而言之,有博雅焉,有清典焉,有绮艳焉,有宏壮焉,有要约焉,有切至焉。夫模范经诰,褒述功业,渊乎不测,洋哉有闲,博雅之裁也;敷演情志,宣照德音,植义必明,结言唯正,清典之致也……至如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标;语清典,则铭、赞居其极;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叙宏壮,则诏、檄振其响;论要约,则表、启擅其能;言切至,则箴、诔得其实。凡斯六事,文章之通义焉。苟非其宜,失之远矣。博雅之失也缓,清典之失也轻,绮艳之失也淫,宏壮之失也诞,要约之失也阑,切至之失也直。体大义疏,辞引声滞,缓之至焉;理入于浮,言失于浅,轻之起焉……故词人之作也,先看文之大体,随而用心。遵其所宜,防其所失,故能辞成炼核,动合规矩。〔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刘善经论体,指文体风格,他把文体风格分为博雅清典等六大类型,而以颂论等十二种文体分别与之配合。其议论与《文心雕龙·定势》颇为接近。他叙述六类风格的特征,写法又与《文心雕龙·体性》相近。他不但叙述六体的特征并指出它们容易产生的缺点,这种议论大约受到《文心雕龙·明诗》以下十篇中“敷理以举统”等项内容的影响,并且也使用了“大体”这个词语来指文章的体制风格。总之,刘氏论文体风格,虽然没有太多发展.但概括得相当明确具体,立论较为完整,可说对前此的文体风格论进行了总结。
唐代诗歌创作繁荣,诗论中言及体的颇多,也常常是指作品的体貌风格。论说前代诗歌有建安体、永明体、齐梁体、宫体、徐庾体等名。大致都是根据作品体貌特征立论。皮日休《郢州孟亭记》云“明皇世章句大得建安体”,是说盛唐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优良传统,富有风清骨峻的风貌。永明体、宫体、徐庾体等名称,都沿袭南朝。齐梁体指兼受永明声病和梁代宫体轻艳诗风影响的体貌。对唐本朝诗歌,也常用“体”字。如杜甫《戏为六绝句》诗有“王杨卢骆当时体”之句;白居易、元稹的一部分诗歌,当时称为“元和体”。“体”都是指诗歌风格特色而言。初唐李峤在《评诗格》中说诗有形似、质气、情理、直置、雕藻、影带、宛转、飞动、清切、精华十体,即十种风貌。盛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中说,“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体也均指风格。中唐皎然《诗式》将诗歌分为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城、闲、达、悲、怨、意、力、静、远等十九体,每体各作简单说明,则比较偏重思想内容的特色。到了晚唐,司空图把诗歌风格分为二十四品,对诗歌风格的探讨更趋细密,只是并没有使用“体”这一名词。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有《诗体》一个专篇,列举各种诗体名目最为繁富。其中一部分是从形式格律来区分的,如四言、五言、七言、古体、近体、绝句以及乐府歌行、杂体诗等。这是属于体裁样式上的分类。另一部分则是着重从风格来区分的,其中又分三类。第一类按照时代来分,有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盛唐体、元和体、元祐体等等。第二类按照作家来分,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少陵体、太白体以及东坡体、山谷体、杨诚斋体等等。第三类大致上是按照流派来分,有边塞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等等。其中不少名称,过去早已习惯运用,如建安体、永明体.元和体、陶(彭泽)体、谢(灵运)体、徐庾体、宫体等等。严羽把它们归纳集中起来,做系统介绍。作为风格意义的诗歌的各种体,在《诗体》中大致都归纳进来了。因此严羽此篇可说是一个总结。稍后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介绍“诗体”颇为详细,其上卷即抄录《沧浪诗话·诗体》,大约即因严羽所论较为详备之故;下卷介绍其他诗体,均从体裁、样式方面区分。严羽对辨别诗歌体制非常重视,他曾说“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答吴景仙书》)。后来有的诗论家受其影响,对辨体一点也颇为注意,明末许学夷更有《诗源辨体》专著,着重论述历代名家诗歌的体制风貌。但总的说来,元明以来文人论文体、诗体,多数从体裁、样式、格律方面进行探讨,论风格之体者较少,也无其新意,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体在我国古代文论中,不少场合是指作品的体貌、风格,它不但标志着某种文体的特殊风格,而且更多地标志着一个作家或一群作家的主要创作特色,在文学史上形成流派,甚至成为某一时代创作的主要倾向,成为时代风格。接下来关于魏晋诗体流变的论述正是在这一“体”的含义上展开的。
〔共八页〕
1
2
3
4
5
6
7
8
上一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