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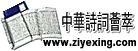 |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 |
|
文/朱光宝 海阔中文网网站整理收录·仅供参考
上编·诗体流变
第五章 五言腾踊
第一节 五言诗溯源
五言诗彬彬之盛大备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见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此后,历经两晋南朝的发展,五言诗终成蔚然大观,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主要的诗体。
前人论五言诗之起源,皆推之姬周时代,《艺文类聚》五十六引挚虞《文章流别论》云:
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
挚虞以《诗经》中《召南·行露》一诗为例,认为五言始于《诗经》,后人率从其说。《文心雕龙·明诗》论五言起源云:“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然一诗之体,即以五言为称名,则如五言之句,仅有半章,不当以五言诗视之。《文心雕龙·明诗》又说:“孺子沧浪,亦有全曲。”刘勰把《沧浪歌》视为完整五言诗。《沧浪》见于两书,一为《楚辞·渔父》,一为《孟子·离娄》。《渔父》的真伪,后世争论很大,可不置论。以《孟子》所引为据,那么《沧浪》当产生于战国时期。其词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诗的一、三句是六言,其中的“兮”字被刘勰认为是“语助余声”,“无益文义”,故欲删落,从而视为五言。但汉语单字单音,字字独立,《诗经》中有很多“语助”一类虚字,如“薄言采之”的“薄言”,怎能视为无益而删取?可见战国时间仍无五言诗。
钟嵘《诗品序》有所论述:“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诗品》举“郁陶乎予心”两例,但也认为“诗体未全”,通篇尚不是五言诗。
今人有以秦始皇时民歌为现存最早的五言四句诗,此说源自《水经注·河水》引杨泉《物理论》云:“秦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拄。”陈琳《饮马长城窟》有此四句,然而后两句并非五言:“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陈琳诗当承秦时歌谣之旧所作。可见杨氏所载,恐怕有所删落,当不得视为五言诗之先例。
既然周秦时代,五言诗体未全,那么将目光投向汉代。两汉五言诗之有作者名始于东汉班固。班固以后,作者世出,连绵于建安。然前乎班氏者有两《汉书》《华阳国志》等所载汉代诗歌,其诗无一有主名者,如《汉书·贡禹传》引武帝时俗语:
何以孝悌为?多财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
到了汉成帝时,五言民谣渐渐多了起来,如《汉书·尹赏传》载: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如《汉书·五行志》载: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花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又如《华阳国志》中所载新莽末国人为谯君黄作诗:
肃肃清节士,执德寔固贞。违恶以授命,没世遗令声。
《后汉书·樊晔传》凉州歌:
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这些无名氏所作五言诗句,足配班作。自汉武以降,其间五言篇章,赓续不绝,洪流浩浩,前乎此,则尚无五言之先例,后乎此,则篇章已多矣。可见,五言诗体发生之起点,应为汉武时期。武帝立乐府采诗夜颂,赵、代、秦、楚各地之歌纷纷涌入都城,新体升入庙堂在当时最为容易,也就促成了五言体产生。
第二节 五言诗篇制
自滥觞于采诗作乐之汉武一朝后,五言诗篇制从句无定数、篇无定制,发展到四句、八句并兴,再逐渐发展成八句为主、八句定型。所谓诗歌篇制,指的是诗歌篇幅的大小、句数的多少,这是诗歌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律诗诞生以前,古体诗在体制上较为自由灵活,篇无定句,句无定字。建安以后,虽是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多种形式并存,但逐渐形成“五言腾踊”的局面,五言诗成为文人最常用的诗歌形式。由此诗歌开始趋向格律化,五言诗的篇幅长短也出现了有规律的变化,齐梁陈三代,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南朝诗人创作的五言诗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合乐而作,采取乐府体或拟乐府体,一类是非乐府体。这两类的篇幅都由长变短,其中八句式出现最多,五言八句式渐成定制,从而为唐代律诗“约句准篇”提供了最佳的句式基础。此中的发展脉络,正如《新唐书·宋之问传》中述评说:“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
研究五言诗篇制的变化,首先须对篇制长短做一界定,以八句为准,八句及八句以下的为短篇,十句至十六句的为中篇,十八句以上的为长篇。
自汉至晋,民间歌谣以三言、四言为主,也有一些五言。五言诗篇无定制,自由灵活,以长篇、中篇居多。汉乐府古辞中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出现不少五言诗,但篇幅长短不定,仍以长篇为主。文人创作的五言诗无论是乐府体或非乐府体,大部分为十六句或二十句以上的长篇,中篇也有一定数量,短篇较少,如《古诗十九首》多在十句至二十句之间。东汉以降,文人开始仿制乐府,至建安,此风渐盛,“三祖陈王,所作皆多至数十篇,文人乐府,斯为极盛”〔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24页〕。当时的乐府诗创作“一似纯出模拟,其实皆属创作,以其题虽旧,而其义则新也。此外亦有自出新题者”,诗句字数上“则极其自由”,“诸体毕备”〔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26页〕。这些乐府诗体制较为自由,多为长篇,如曹操存诗二十一首皆为乐府诗,有四言、五言、杂言三体,其中五言乐府包括《薤露》《蒿里行》《苦寒行》等等,这些诗有的为残句,有的为重章叠句,大多篇幅较长。其他文人五言乐府也绝大部分属于长篇,非乐府体的五言诗也以中、长篇为主。十六句以下的中篇随着五言诗创作的日益兴盛而逐渐增多:曹植五言诗最多的是十二句和十六句。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中以十句、十二句诗数量为胜,陆机的拟古诗多在八句至十六句之间,左思的《咏史诗》则以十二句为主。相形之下,汉魏时期五言短篇屈指可数,四句的有《长安为尹赏歌》《巴郡人为吴质歌》《咏谯君黄诗》和《刺巴郡郡守诗》四首,八句的仅有《凉州民为樊晔歌》一首。
两晋时期,五言四句体为越来越多的文人使用。傅玄、张华、陆机、张亢、李充、卢谌、郭璞、庾阐、袁宏、孙绰、王献之等均留有此类作品。其中,孙绰《情人碧玉歌二首》之一:“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愧无倾城色。”王献之《情人桃叶歌二首》之二:“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两首皆为脍炙人口的佳制。东晋时期有一桩文坛盛事,王羲之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组织了兰亭雅集。或由于天朗气清,或因为茂林修竹,雅集参与者多达四十一人,在他们创作的诗歌中有四言十四首,五言二十七首。孙嗣、庾友、曹茂之、王玄之等十四人采用的均为五言四句体,其作者和作品的数量都占了一半以上。众人在同一次聚会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五言四句体,绝不是偶然现象,它至少表明五言四句这一体裁在当时的文人中已相当流行。同时,他们的创作已经超越了对歌谣乐府的模拟,成为独立的体裁──文人五言古绝。这一点,从他们聚会中写的《兰亭诗》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晋、宋之交,古今诗道升降之大限乎?”〔胡应麟撰《诗薮·外编卷二·六朝》,中华书局,1958年,第143页〕胡应麟这句话的着眼点在于诗风的转变,此处借以说明“晋宋之交”也正是诗歌篇制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晋末开始,历经刘宋至齐永明以前,五言诗仍以中、长篇为多,但篇幅有所缩短。五言四句的名篇佳作时时涌现,八句式短篇略有增加,尽管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已经呈现出一些自己的特点。
此时期出现的清商曲辞大部分为五言四句诗,如《碧玉歌三首》《乌夜啼八曲》《襄阳乐九曲》等。这些五言乐府多为活跃在民间的文人所作,主要在民间传唱,后来渐渐影响到文人创作。我们从陶渊明以及“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的乐府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仍以中、长篇为主,但显示出从中、长篇向短篇过渡的趋势。如谢灵运的五言乐府多为长篇,《泰山吟》是唯一一首五言八句乐府诗。值得注意的是,《玉台新咏》著录了谢灵运两首模仿当时民歌的《东阳溪中赠答诗二首》,皆为五言四句。鲍照大力创作乐府诗,形式有五言、七言、杂言,其中五言拟乐府以二十句为最多,有八首。然而鲍照乐府诗也有不少短篇,尤以四句式为最多,其中《扶风歌》《箫史曲》为五言八句式,《王昭君》《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幽兰五首》《中兴歌十首》等都是四句。
齐梁之际乐府民歌的兴盛,标志着五言四句体的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南朝民歌体制上的特点是多五言四句。在现存的四百多首作品中,只有小部分是四言、七言和杂言,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是五言四句体。这对后来五言绝句的正式定型,无疑起了重要作用。这种短小易诵的体制,配上当时绮靡艳丽的新声,很容易便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和喜好。刘宋以来的作家,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底层文人,几乎没有不创作这种诗体的。据《南史·曹景宗传》记载,大将曹景宗破北魏军,凯旋班师,“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惟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即便终日驰骋沙场的武将也采用这种诗体进行创作,足见其流行和普及程度。鲍照一人就有五言四句三十八首之多,充分说明这种诗体已获得文人的重视和欣赏,并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
五言八句也在同时发展。这一时期写作乐府诗较多是沈约和萧纲。沈约的五言乐府诗中,有四句式七首,六句式八首,八句式十二首,八句以上中、长篇共十三首。萧纲有短篇四句式十二首,六句式九首,八句式二十七首,八句以上中、长篇共二十一首。可以看出,两人的五言乐府短篇数量大大超过中、长篇,四句、六句及八句式运用较多,特别是八句式位居榜首。
永明时期的五言短篇在数量上已经多于中篇与长篇。永明以后五言诗中长篇进一步减少,吴均仅有长篇三首,即三十四句的《答萧新浦诗》、二十句的《酬别江主簿屯骑诗》、十八句的《采药大布山诗》。萧绎只有四首,萧纲虽有十五首,但在其乐府诗中仅占微小比例。
南朝末期,五言诗中仍是短篇最多,其中八句式的发展明显超过四句式,成为诗人的首选。如乐府诗,张正见八句式有三十二首,四句式仅一首;陈叔宝八句式二十八首,四句式十一首;徐陵八句式十一首,无四句式;江总八句式十八首,四句式一首;王褒、庾信无四句式。非乐府体诗情况类似,四句式远少于八句式。五言八句成为五言诗最常见的形式。
第三节 五言演变原因辨析
五言篇制的演变是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出现的必然现象,其中既有时代背景、社会风尚、诗学思潮、审美时尚在内的外部原因,又包括文学传承、诗歌技巧等诗体内部的因素。
晋室南渡之后,“新声”普遍流行,整个社会开始沉湎于声色享乐之中。五言四句诗的兴盛,自然受到了乐府民歌,尤其是吴声、西曲的影响。《世说新语·言语》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妖而浮”说明吴声的特点,“共重”说明当时喜爱者已不在少数。《南史·良政传》载,齐武帝永明年间,“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由此不难想见南朝社会歌舞之盛。《乐府诗集·杂曲歌辞》说:“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言废矣。”这段话说明,南朝乐府民歌在音乐上的特点是哀淫靡曼,繁艳浅近,在歌词内容上则多为男女情歌,所谓“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乐府诗集·子夜春歌》〕。而且,这种香词艳曲愈演愈烈,已成为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上自宫廷王室,下至民间市井,几乎无处不弥漫着这种靡靡之音。五言四句诗短小精致,音律和谐,辞藻秀美,情韵悠长,与南渡后乐府民歌一脉相承。
至齐梁时期,以帝王和各宗室为中心形成不同的文学集团。文人宴会游嬉之际少不了奉和赠答,在有限的时间内,也只有选用适当的篇制,才便于精心构思,运用技巧,展现才华。关于这方面的事例,史书记载颇多,如《梁书·文学传序》载:“(高祖)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胭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唐·姚思廉撰《梁书·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第685页〕在这些活动中,诗人们往往依某题应令或依某曲即席进行创作。又据《南史·王僧孺传》记载:“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唐·李廷寿撰《南史·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3页〕从中可以看出,这类文学活动颇有相互切磋诗艺,较量诗才的意味。所以多同赋一题,同用一形式,且限韵作诗,以四韵为一停顿,两句一韵,四韵即八句,以比较诗思的敏捷、诗才的高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采用同样的诗歌形式,才容易比较出各人的才学高下。文人聚会、游玩、送别等场合所写奉和、应教或赠答诗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全是五言八句式。“在这类从多种角度描写同一主题的系列诗中,五言八句的形式相当有效地发挥了机能。”〔日·兴膳宏《五言八句诗的成长和永明体诗人》,载《东方丛刊》2001年2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说明八句式凭借它长短适中的篇制优势,从各种诗歌篇制中脱颖而出。不仅最适宜即兴创作,使诗人在有限的时间内调动才思,也最适宜传达情感,既不因太短而不足以说明心意,也不会因太长而显得啰唆累赘。南朝后期,用于酬赠唱和的五言八句式诗日益增多,更说明了这一篇制的优势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
从诗体发展的内部因素来看,诗歌篇制长短与对偶技法的发展有关。六朝前期诗歌多为中、长篇与讲究排偶、对仗句较多有直接关系,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诗大量用排偶,极尽雕刻之能事,有时全篇排偶,如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颜延之《赠王太常僧达诗》、鲍照《登庐山诗》等,都是长篇。《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谈到:“谢灵运的山水诗常以辞斌的铺陈之法写作,因此一般篇幅较长,描绘细致。《明诗》说刘宋山水诗‘俪采百字之偶’,五言诗要达到百字之偶,至少需二十句,说明其篇幅之长。谢灵运达到百字或超过百字的篇章的确比较多。”〔王运熙、杨明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9页〕。元嘉诗歌对偶句数量较多与当时对偶技法处于摸索阶段有关。朱光潜指出:“律诗第一步只求意义的对仗,鲍、谢是这个运动的两大先驱。”〔朱光潜著《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9页〕试看大谢《登上戍石鼓山诗》:
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
汩汩莫与娱,发春托登蹑。欢愿既无并,戚虑庶有协。
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日末涧增波,云生岭逾叠。
白芷竞新苕,绿萍齐初叶。摘芳芳靡谖,愉乐乐不燮。
佳期缅无像,骋望谁云惬。
首四句近似隔句对,每两句解说一个意思;七、八两句与九、十两句用对都属于互为意义的对句,并列地说明一个意思;再下四句铺陈景色。大谢诗中常常出现对句中两个句子同说明一个意思的情况,像这类用对的方法在颜诗与鲍诗中也可轻易发现。譬如颜延之《拜陵庙作》:“陪厕回天顾,朝宴流圣情。早服身义重,晚达生戒轻。否来王泽竭,泰往人悔形。”鲍照《从临海王上荆初发新渚诗》:“收缆辞帝郊,扬棹发皇京。狐兔怀窟志,犬马恋主情。抚襟同叹息,相顾俱涕零。”这些对偶句都是上下两句同说明一个意思。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诗歌有不少对偶的上下两句意思相近,偶然还会出现两句内容完全一样的“合掌”现象,当时诗人对于对偶的运用技法还处于初级阶段,一味追求排偶,对仗句子多,诗歌板滞少变,篇幅冗长,结构松散无重心。至发展期,有的对偶句上下两句意思由相似的并列关系变为进一步说明的递进关系,或两句句意相差甚远。小谢有《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己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与上举大谢诗相比,小谢此诗中的对偶句句意多为进一步说明的关系,如首二句,上句说前路遥远,下句说归途延伸;三句说归舟渐近,四句说江树远去;五句说旅途疲倦,六句说久已孤独。其他对句也属于此种关系。萧纲《送别诗》:“烛尽悲宵去,酒满惜将离。”上句哀叹夜已去,下句惋惜将别离,下句对上句有进一步补充说明的关系在内。这种递进关系使诗歌内容的表达与结构都更加紧凑,促使诗篇更加浓缩。
从永明体开始,诗人用对更为精巧,《颜氏家训·文章》中有“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0页〕指出齐梁诗歌对偶讲究字义与声律的对仗。如沈约、谢脁、吴均、萧纲、阴铿、何逊等人诗歌用对,技法更高明,对偶种类更多。日本赴唐僧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一书中所提到的二十九种对,大部分都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找到。重视对仗运用的技法与探讨声律相互促进,而诗歌篇制大小对于对仗的工整与声律的协调又有一定的影响。诗歌篇幅过长,对偶句多,声律重复单调,体现不出诗歌“精妍新巧”之美,追求对仗的新巧则有助于诗歌句式的凝练、结构的紧凑与篇幅的适中。诗人在实践中摸索出用对技巧:对句上下两句句意须相差较远,位置应集中在中间部分,既易于展开描绘,又形成一个重心,固定首尾部分和诗歌结构。诗歌篇制随着对仗技巧的发展而变化,由二十句的长篇逐渐趋向于八句的短篇。永明体与宫体诗对偶日趋精工,声韵和谐,篇制也因此而愈见精练,多在四句至十四句之间。由此可见对偶的精工整饬直接影响到诗歌篇幅的缩短。在诗歌日趋骈偶化的过程中,八句式越来越凸显出它的优势:最适合于对偶句子的安排与声律的对仗。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曰:“自古诗渐作偶对,音节亦渐叶而谐。宫体而降,其风弥盛。徐、庾、阴、何,以及张正见、江总持之流,或数联独调,或全篇通稳,虽未有律之名,已寝具律之体。”〔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页〕这一段话指出了南朝诗歌讲究对偶与声律的运用,而八句式篇制与对偶、声律的结合,便逐渐接近五律的体制。
〔共八页〕
1
2
3
4
5
6
7
8
上一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