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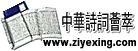 |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 |
|
文/朱光宝 海阔中文网网站整理收录·仅供参考
上编·诗体流变
第七章 格律肇始
第一节 早期诗律演进轨迹
中国古代诗歌,由非格律诗到格律诗的转变,永明体是一个关键。实际上,在永明体以前,汉语诗歌早出现了诗律因素。在汉语诗律的历史进程中,节奏与韵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韵律指诗歌的用韵规则,其中押韵为重要因素。《诗经》中,押韵较为普遍多样。先秦诗歌中,韵字平押平、仄押仄,在仄声中还区别了入声押入声,上去声押上去声,也就是声调相同的押韵规则。两汉是诗律的探索期,汉代诗人似乎有意地探索和运用“声调交互”的押韵方式。西汉时期的诗歌已出现五言诗句二、四异声的现象。到东汉,文人五言诗中声调交互已成为普遍现象。总结起来,汉代文人对声律的探索有两大特点:首先,以句为单位,声调的交互与律句的建构同步进行;其次,由律句过渡到律联。此外,对韵律的探索,是韵式趋于统一,基本韵式为隔句末用韵,平声韵字居多,也有押仄韵的,有转韵一次或多次的现象。
到汉末,相对而言,诗律探索进入停滞期。不过,曹植对诗律的探索成绩仍属辉煌。其中原因,既出自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也受到“梵呗”的影响。《魏志·武帝纪》记载曹操的文艺修养说:“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引《异苑》的记载说:“陈思王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有诵经声,清遒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释慧皎《高僧传·十三经师论》也记载:“梵吹之起,肇自陈思。”为增进诗歌语言的谐和美,追求平仄的调协,音韵的契合,曹植吸取众长,丰富了诗篇韵律,其诗中律句、律联大量出现,为诗律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曹植的诗律探索不仅见称于当世,也影响到西晋诗人。严可均《全晋文》辑有陆云给陆机的信,其中提到,李氏云“‘雪’与‘列’韵,曹(植)便不复用”。人亦复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难得正。”由此可见,西晋诗人把曹植的遣词协韵视为范例。
西晋初年,文人探索诗律之风颇盛。陆云就不止一次地以书信形式与乃兄陆机讨论过有关问题:
《喜霁赋》:“俯顺习坎,仰炽重离”。此下重得如此语为佳,思不得其韵,愿兄为益之。
“彻”与“察”皆不与“日”韵,思惟不能得,愿赐此一字。
《九悲》多好语,可耽咏,但小不韵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归高如此,亦可不复更耳。
《诲颂》兄意乃以为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韵,不知差前不?不佳者,愿兄小为损益。
这几条都是讨论诗律的。这种研讨诗律的文学氛围在西晋甚嚣尘上。《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一个故事,陆云(陆士龙)至洛阳,在张华家遇荀隐(荀鸣鹤),张华说:二人皆为名士,不可以常语相称。于是陆云自称“云间陆士龙”,荀隐接着自称“日下荀鸣鹤”。这一对答,是一副极音声迭代之妙的对联。陆云的一句是“平平仄仄平”,荀隐的一句是“仄仄平平仄”。陆机的文艺理论专著《文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赋》中总结五言诗的创作经验时,提出要研究声音的协调,并以色比声,借以说明声音调配的道理。
虽然魏晋二百年间五言诗的创作较两汉繁荣,然而魏晋文人五言的律化仍停留在一句之内与两句之间,还没有深化到联与联之间的篇律构建阶段。对先秦至魏晋时期,汉语诗律探索的过程描述,可以参阅秦惠民:《中国古代诗体通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7-252页〕。
南北朝是诗律的形成期,其标志则是永明体诗歌的出现。“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483-493),永明诗体就初诞于这个时期,由沈约(441-513)、谢脁(464-499)、王融(467-493)等奠基;又因主创人沈约自齐入梁,至徐陵(507-583)、庾信(513-581)、张正见(约527-582)等而成熟,故亦称齐梁体;旋至清末王闿运(1833-1916)编《八代诗选》(汉至隋)又将其命名为新体诗,以此区别于其前的古体诗(五言古体),以及其后初唐成熟的近体诗(五言近体)。永明诗人建构了强调声韵格律,讲究对仗工整,篇幅短小(以八句型、四句型为主)的一种五言诗模式。沈约等人提出的“四声八病”说是其格律的基础理论,永明体的形成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反映了诗歌走向格律化的自然趋势。
第二节 永明体形成背景
对永明体的考察,我们先看其形成的背景,再谈其在格律化方面的贡献。
永明年间,社会稳定,士民富庶。《南齐书·良政传序》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是南齐宗室,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作家们有潜心创作、钻研声律和诗歌创作规律的良好环境。同时,统治阶级重视招徕文士,还发动集体文学创作,切磋技艺,共同探索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当时至少有四个比较大型的文学集团的存在:卫军将军王俭集团、竟陵王萧子良集团、豫章王萧疑集团、随王萧子隆集团。其中萧子良集团存在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永明体诗人绝大多数出自该集团。
在社会变迁的同时,诗风也在变化。《文心雕龙·明诗》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从西晋起,诗风便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除东晋经过了一阵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外,诗风便由稍入轻绮而深入轻绮了。“采”是一天天缛下去,“力”是柔得几乎没有了。追求采缛的结果,是发展到声律的协调。
晋世文人在逃避现实和追求玄远的过程中,首先从大自然中寻求到了刺激。从山水诗起,已然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诗人极力追求诗歌的形象化,大量运用譬喻状词。《文心雕龙·物色》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诗品》言谢诗“故尚巧似”,颜诗“尚巧似”,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都是指善用譬喻状词等说。写一种新鲜的山水景物,自然需要很多的状物喻形的形象语言,就是这种风气形成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偶句和声色的讲求。《文心雕龙·声律》云:“是以声画妍媸,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山水绚丽多姿,想要极貌逼真,诗中必定要极富声色。谢诗中如“白云抱幽石,绿条媚清涟”(《始宁墅》)、“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石门心营所住》),《诗品》称其“富艳难踪”,也就是声色讲求得多的意思。这是文学受赋之影响,用铺陈的俪典新声来写诗,所谓“世运相乘”。声色字句要调整和谐,于是俳偶句增多。“上句写山,下句写水”,“上句写闻,下句写见”,对偶浑然天成。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云: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祈祈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徵在今。
这首诗除“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二句外,全诗为对偶句。此类例子颇多。对偶既多,用事也更堆叠。
钟嵘《诗品序》云:“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名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这种风气从颜延之开始,下至齐梁,愈来愈趋极端。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南齐史·任昉传》云:“晚节转好作诗……用事过多,属诗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其实不只任昉如此,《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谓“辑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是当时文人的共同风气。《陈书·姚查传》云:“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时重其富博。”当时评价文人以富博为高,文人当然也以富博自矜,以表现自己的高贵风雅,帮助仕途。文学内容的空虚,又亟须形式的繁缛华丽来装饰,那么诗文中的唯以数典用事为工,自然蔚为风气。史称沈约“博物洽闻,当世则取”,崔慰祖称刘孝标为“书淫”也是说的这个意思。
当时风气,文人们聚会时互相隶事。《梁书·沈约传》云:“约尝什宴,至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文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顺着这种极端追求形式的方向发展,在内容贫乏单调的情形下,和数典隶事的风气完全属于同一原因,如果还可以增加形式的华美,自然也会令文人们向风。
于是,顺着山水诗“极貌写物”的注重声色方向,进一步凝聚到了永明体的声律说,这种追求音乐式的和谐美,正和追求数典隶事属于同一动机,尽管转变了角度。这些都属于形式美,其发展高峰就是后来的四六文和近体诗。发展至此,凝固为一种固定的格式:隶事代语和平仄的韵脚,这都是多年来追求结果的积累。
同时,佛教活动大盛,导致了“四声”确立和“声律论”的产生。
晋初,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认为文章应在音节上抑扬交错具有和谐之美。刘宋之初,范晔在《后汉书·自序》中说他“性别宫商,识清浊”,表明已朦胧地感到文字的声音审美特性。四声论创立前,曹魏人李登撰《声类》、晋人吕静著《韵集》均用五声命字,唐封演《闻见记》说:“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魏书·江式传》论到吕静《韵集》,指出这五声是“宫商角徴羽各为一篇”的,看来是由音乐的五声转化过来的。前人在声韵上累积了一定成绩,而转读佛经的影响有力地促成“四声”在永明年间被明确。
释慧皎《高僧传·译经下·论》明白地讲道,佛经东传,“夷夏不通,音韵殊隔,自非精括诂训,领会良难”。支谦、竺佛念等“妙善梵汉之音”,译经时“更用此土宫商,饰以成制”。后来鸠摩罗什和弟子们“复恨支、竺所译,文制古质,未尽善美”,遂为重译。也就是说,旧译所饰的汉语音韵,是依照古诗古乐府的宫商,而古今音声变迁,使旧译难以再现原著风格而成诵,不合“方便”。新译佛经成于姚秦的长安,北地言声和江南音调的地域性差异,存在着又一种“殊隔”,给佛教在南国传播带来同样的不“方便”。“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高僧传》卷一三〕。“所谓歌诵法言,以此为音乐者也”〔《高僧传》卷一二〕,即经译音乐化的语音构造,对众庶参味具有移情功能的“五利”。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宋齐之间“人人致意,补缀不同。所以师师异法,家家各制。皆由昧乎声旨,莫以裁正”〔《高僧传》卷一三〕。因此可以说,萧子良招致名僧,造经呗新声,显然是要结束“师师异法,家家各制”的纷乱,形成一致而达成“方便”。此外,“昙迁、僧辩、太傅、文宣等,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依旧法,正可三百馀声”〔《高僧传》卷一三〕。这个数字与隋陆法言《切韵》相较,虽仍有不小距离,却也显出靠拢口语的倾向。民歌俚曲俗谣同文人乐府一样,是造经呗新声的主要参照形式,但也暴露出它们自身的问题。一方面,文人乐府的声律,刘宋的律尺全同西晋,音乐形式高度“拟古”,极力于高古淳雅。另一方面,民间新声“务在焦杀,不顾音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王僧虔《乐论》〕,十分粗糙散漫。文人乐府和民歌的音声构造,也同于佛教经呗,面临着从发展的角度加以整理更新的需求。这种努力既为造经呗新声提供借鉴经验,也是对它的促动。可以说,萧子显所谓“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对文人乐府和民歌俚曲去长补短,达成“不雅不俗”的折中,恰应是诗歌“新变体”和“经呗新声”声韵建构的同一原则。所以,经译语音结构的音乐化更新整饰,与其文辞的现代化,属于佛教通俗化内容之一的两个相互联系的侧面。
齐武帝永明七年(489),竟陵王萧子良大集僧侣于京城,造经呗新声,实为辨明“四声”的一大动力,而周颙、沈约也曾参加子良的考文审音的工作,所以“四声”明确于此时及周、沈等人,并非偶然。
第三节 永明体对诗律初建的贡献
《文镜秘府论》天卷引隋人刘善经《四声指归》云:“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南史·周颙传》说:“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封演《闻见记》说:“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皆称才子,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论述了四声产生之因,认为这是从转读佛经之三声转化而来的:“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列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陈寅恪《四声三问》,载《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收入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67-368页〕。这确是不易之卓见。今人吴相洲却认为尚无直接证据表明永明体的产生就是受到了佛经转读的影响,而二者都是与音乐有关的一种活动,所遇到的问题都是要解决字与声(词与乐)的配合问题,这或许是二者的关系所在。吴相洲《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再探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第62-69页〕。
“四声”既明,文人们乃积极有意识地在创作时调和声韵,以加强作品的音乐性。而沈约等更从调音的探索中,总结出使音节失调而须避免的一些现象,乃有所谓“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四声八病”说也称“永明声律说”,以往有关书籍称引不一:称引最多的,是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颇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世呼为‘永明体’。”李延寿的《南史·陆厥传》有一段文字与此相类,不过多出了“八病”中的四种内容。这两段文字末尾都提出了“永明体”,“永明体”之称,应以此两段资料为最早。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强调文章中调协音节抑扬的重要: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宫羽”就是指平仄。《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云:“元氏(兢)曰:声有五声,角徵商宫羽也。分于文字四声,平上去入也。宫商为平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角为入声。”可知诗律上的所谓“宫商”,就是古音律上的“五声”,是以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来配汉字的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这种配法不仅牵强,在数目上也是不对应相合的。有鉴于此,南齐李节撰《音谱决疑序》作了折中调和性的说明:“商不和律,盖与宫同声也。五行则火、土同位,五音则宫商同律。”沈约所说的“浮声”,就是指“清音”即平声;“切响”就是“浊音”,即上、去、入三声。“一简”指一行,即五言诗的一句;“两句”,两行,指五言诗的一联。所谓“轻”、“重”亦指平仄。顾炎武《音论》云:“其重其疾,则为入为去为上;其轻其迟,则为平。”以上所述,均为“四声”方面的问题,是永明声律说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外,还有“八病”的问题。《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引用沈约《答甄公论》明确提到了“八体(病)”的问题:“作五古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这五句话前三句,是说作五言诗的人善于用平上去入四声,则诗篇韵律流畅美好;而能通晓“八体”,则韵律参差有序。这里的“八体”是否即为“八病”呢?《文镜秘府论·西卷·论病》一节中云:“八体、十病、六犯、三疾,或文异义同,或名通理隔。”据此可知,“八体”即“八病”之异名,沈约本人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八病”的理论。“八病”的具体内容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现分别阐释其内容:
一是平头,上尾。这是指两句五言诗句头句尾同声之病。先说平头,《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谓平头云:“平头诗者,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犯平头。”这就是说,五言诗上一句的开头两字,不得与下一句的开头两字平仄相同,若同,则是犯了“平头”之病。“上句第一、二字是平声,则下句第六、七字不得复用平声。”这条病犯的讲究,是为了防止一联之内上下两句开头两字字声相同的缺点。它是“两句之内,轻重悉异”理论的具体化,是永明体诗的一条重要构律规则。齐梁以来的诗人在五言诗创作中十分重视这条规则,成为后来格律诗黏对律中“对”律的重要内容。因此它在调声术中叫做“换头术”,即一联两句之间,前句平声字开头,后句必须用仄声字开头。反之亦然。因为开头的“起”字是什么声调,决定全句乃至全诗的声律安排,显得特别重要。
再说上尾。《文镜秘府论》论上尾病曰:“或名土崩病。上尾诗者,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名为上尾。”“上句第五字是平声,则下句第十字不得复用平声,如此病,比来无有免者。此是诗之疣,急避。”《文镜秘府论》还说:“齐梁以前,时有犯者。齐梁以来,无有犯者。唯连韵者,非病也。如‘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是也。”上尾也是一条重要的构律规则,是“两句之内,轻重悉异”的理论在句尾规定的具体化,即要求上下两句最后一字的平仄必须相对。句尾是用韵的地方,是全句诗节奏的终点,一平一仄可以突出和谐的韵律效果,所以上尾被认为是一条重要的不能违反的规则。上尾病最严,刘知几《史通·杂说》就说过:“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
二是蜂腰、鹤膝。《文镜秘府论》云:“蜂腰诗者,五言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央细,似蜂腰也。”“鹤膝诗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以其诗中央有病。”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永明体与声律问题》一节中认为,《文镜秘府论》中的这一记载“不很可信”,理由有三:“一、与蜂腰鹤膝的名称没有关系。二、永明体的声律只讲两句间的关系,此却论到第三句。三、后来的律诗不以此为病为犯。”郭先生的怀疑是可信的。因为“蜂腰”一词的含义是两头大中间小,这与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的内涵颇不一致。这种名实不符的情况,近人刘大白在《旧诗新话》中曾推测说:“蜂腰是指第三字和第八字同声的病。”因为“第三和第八字都在五言句的腰上”。再说鹤膝以第五字与第十五字同声为病,这也名实不符,因为永明体的声律只讲两句五言诗之间平仄关系,而不是第三句,且第五字与第十五字均为五言诗句之“尾”,怎么能称为“膝”呢?据此,刘大白认为:“鹤膝是指第四字与第九字同声的病。”因为“第四字、第九字都在五言的膝上”。这个推测也是言之成理的。因为蜂腰是一联之内第三字与第八字同声相犯,鹤膝是一联之内第四字与第九字同声相犯,符合永明声律说的基本精神,属于永明声律说的基本内容。
三是大韵、小韵。《文镜秘府论》关于“大韵”的解释为:
大韵诗者,五言诗若以“新”为韵,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邻”“身”“陈”等字,既同其类,名犯大韵。
大韵是指一韵(联)之内(两句)所犯之病。韵字之外的九字中不得有任何字与韵脚叠韵、同声。《文镜秘府论》关于“小韵”的解释为:
“小韵诗,除韵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为犯小韵病也。”小韵是指一韵(联)之内,韵脚之外的九字,相互间不得有叠韵、同声之字。若连用两个叠韵字,则为例外:“若故为叠韵,两字一处,于理得通,如‘飘飘’‘窈窕’‘徘徊’‘周流’之等不是病限。”
四是旁纽(大纽)、正纽(小纽)。《文镜秘府论》关于“旁纽”的解释为:
旁纽诗者,五言诗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鱼”“元”“阮”“愿”等之字,此即双声,双声即犯旁纽。
《文镜秘府论》关于“正纽”的解释:
正纽者,五言诗“壬”“衽”“任”“入”四字为一纽;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如此之类,名为犯正纽之病也。
王运熙等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认为,沈约、刘滔所谓“纽”相当于宋元以后等韵学上的“字母”。而隋与唐初刘善经、元兢所谓正纽、旁纽,其实只相当于沈约、刘滔所谓的小纽一种病。即一韵之内有两字(或两字以上)在四声一纽内,且不相连,为犯正纽。如“我本汉家子,来嫁单于庭”,“家”、“嫁”在同一纽内,即声母韵母均相同,只是声调不同,便是其例。若一韵内有两字(或两字以上)不在四声一纽内,但其声纽相同,则为犯旁纽。如“壮哉帝王居,佳丽殊子城”,“居”与“佳”,“殊”与“城”虽是双声,但不在四声一纽之内(亦即韵母不同),即犯旁纽。今人论八病,多承此说。其实沈约、刘滔之意并非如此。
“八病”之中,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均是声调方面之病,是声律方面的问题;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则是声母和韵母方面的病,是韵律方面的问题。后人在五言诗创作中应用这八条规则时,视前四病为重,严格遵守;后四病为轻,宽松得多。因为,诗律以声律为重,韵律方面主要讲究的是用韵及韵式,即令不能做到“音韵尽殊”,也不影响整个诗律的格局。“八病”之说的缺点,也和永明体的缺点相似,即不能超越两句(一联)的范围,而成为两联(四句)的诗律规则。
永明体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由非格律诗到格律诗的过渡形态,其出现是沈约提出的声律理论在五言诗创作中加以运用的必然结果。“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解决了律句和律联的构造问题。为了保证这种“异音相从”的声律结构不被破坏,又提出“四声八病”的同声相犯的防范措施。
永明体诗律是以一个诗联为范围来安排声律的,安排的原则是立足于字声相异,这就避免在两句之末出现同声字的现象。因此,永明体诗格式有两种:
一为平起仄收式: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一为仄起仄收式: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据永明体诗作的考察分析,其格律特点有五:一是永明体诗每联两句平仄相对,相邻两句也平仄相对,故称之为“对式律”。二是以对式律组成的诗,逢单句平仄相同,逢双句平仄亦同。三是对式律诗首句严格规定不准押韵,且不准用平声字收尾。四是对式律诗是以一联为单位安排诗律,原则上立足于字声相异。五是对式律诗单调少变,诗行越多,读起来越觉乏味。由此可知,永明体诗在格律上单调少变机械重复,是它的主要缺陷。实际上,南朝至隋朝的文人八句五言诗中,几乎没有一首纯粹的永明体诗,有关书籍所称引的“对式律诗”、“八句式(齐梁体诗)”均非纯粹之作。
永明体诗律,是以声律的规律性变化为其特点的。由于永明体诗人发现了汉字“音声迭代”的特点,从而提出“一句之中,平仄相间,一联之内,平仄相对”的构律规则,还提出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之病,这些均属于声律范畴的问题。若考察永明体诗的韵律问题,与此前的古体诗相比,只能说是有所变化,但变化无多。如押韵和韵式,语词和对仗等方面,袭旧者多,创新者少。诸如隔句押韵,一韵到底,本韵相押,都是古体诗在韵律方面已形成的格式。永明体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严密一些罢了,说不上有什么新的创造。但沈约等人提出的声律论的影响是很大的,钟嵘《诗品》言及此事时说:“王元长创其首,谢脁、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从这段文字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文士将声律视为衡量五言诗优劣的一大标准。这种风气不仅弥漫南朝文坛,也风靡于北土。据刘善经《四声指归》说,北魏孝明帝继位之后,“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及徙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益以千数。”可见声律之风在北朝盛极一时。直至唐初,论声韵病犯之人的作品仍为数甚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四声八病说终于演变成唐代律诗的格律,西汉以来的古诗律化过程至此结束。
永明体诗作的成就并不高,大名鼎鼎的“竟陵八友”大都留意于诗歌的形式,忽视了思想内容和真实情感的表达,只有号称“永明之雄”的谢脁,上承曹植,下继谢灵运,诗歌善于警句发端,清新流畅,为后人所仰。
总结起来,永明体的特征如下:第一,讲求声律,用韵相当考究,其主要表现为押平声韵者居多,押本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接近唐人。第二,诗的篇幅已大大缩短,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也有一些是五言十句的。第三,讲求写作技巧,讲求骈偶、对仗,律句已大量出现,有些典故很自然地融入诗中。第四,革除了刘宋时元嘉体诗痴重板滞的风气,追求流转圆美和通俗易懂的诗风。第五,讲求诗首尾的完整性,讲求构思的巧妙,追求诗的意境,写景抒情有机地融为一体。
第四节 宫体诗在格律上的发展
然而,永明体诗立足于一联(两句)之内的声律安排,对于四句或四句以上的诗,缺乏一种整体感,诗行越多,缺点就显得越加突出。随后出现的“宫体诗”在补救其缺点的基础上,对汉语诗歌的格律化进程作出了两点贡献:一是在律诗的对式联结基础上探索出了“黏式法”,基本确立了五言近体诗的法度;二是很多诗中使用了拗救,赋予后来的近体诗以灵活的变化形式。
宫体诗为一种侧艳诗,早在宋齐之时便形成,梁陈为全盛期,隋至唐初为其余波,后世对“宫体”的界说大体以梁简文帝、徐摛为主。《梁书·简文帝纪》记载:“太宗(简文帝)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梁武帝)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彩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东阿。’及居监抚,交纳文学士……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梁书·徐摛传》:“及长……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为)晋安王纲(后之简文帝)侍读……王总戎北伐,以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摛出。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书记,寻带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萧衍)闻之怒,招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由此可知,“宫体”之名,是简文帝入主东宫后,时人对简文帝及徐摛等人“新变”、“轻艳”文体风格的称谓。宫体是一种具有“轻艳”风格“新变”的文体,宫体诗为萧梁一代以纤巧绮丽的字句,作求新求变的诗歌。
大通三年(531),萧纲入为皇太子,他不仅带头写宫体诗,而且还提出公开的理论主张:“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出入其门下的宫廷文人庾肩吾、庾信、徐摛、徐陵等,奉承其旨意,遂大力煽扬宫体诗风。宫体诗“新变”审美主张,是对建安风骨的否定,并带来了诗歌内容、形式上的革新,进而对唐诗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宫体诗流行既久,简文帝遂命徐陵撰《玉台新咏》凡十卷,所录诗有许多写女子生活情景与情感活动,选录汉至梁各家艳诗,以清新流丽者为主,间录有民间歌谣,令人耳目一新。刘肃《大唐新语·方正》说:“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孙德谦《六朝丽指》亦曰:“隋志所谓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是也。”过去描写女性美的诗歌,多半较为含蓄简括,写及男女之情也多以夫妇为对象,征夫怨妇为常见主题。宫体诗却多以宫姬、倡女为对象,细腻地刻画人体服饰、歌舞游乐的情景,或描写女子的哀怨心绪,写男女之情也都以直笔书写,因此常招致后世“浮薄之艳”、“滞色腻情”的讥评。
《北史·文苑传》批评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骋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义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陈代何之元在其《梁点总论》中亦评道:“(萧纲)文章妖艳,隳堕风典,颂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斯乃文士之探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虫之技,非关治忽,壮士不为,人君焉用。”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亦说:“梁简文帝伤于轻靡。”明陆时雍《诗镜总论》云:“诗丽于宋,艳于齐……浮薄之艳,枯槁之素,君子所弗取也……简文诗多滞色腻情,读之如半醉酣情,恹恹欲倦。”〔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台北:木铎出版社,1981年,第1407页。〕清代学者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惟以艳情为娱,失温柔敦厚之旨。”当代学者李泽厚、刘纲纯在《中国美学史》中称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高级色情文学”。
宫体诗的产生有深刻的时代文化背景。南北朝对峙二百余年,政治中心和文化重点都南移到长江流域。晋室南渡后,南朝政权偏安江左,不肯以中原为意,社会风习颓废腐败,帝王贵族豪侈淫逸,一味沉溺享乐、流连声色。文士骚客投其所好,无不各逞才华,竞艳争奇,宫体诗便在这样的环境下滋生发展起来。
而江南“委巷中歌谣”──吴歌西曲更是对宫体诗的艺术发展影响巨大。建业一带,文物之盛,衣冠宫柳相属,秦淮商女声歌不辍,“吴歌”遂蓬勃发展。而西曲流行的地区,为荆郢樊邓一带,是长江中游、汉水流域之重要城市,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商旅往来于建业及江陵、襄阳间,旅途劳顿,颇需歌舞声色以娱乐,歌伎倡女应时而生矣,西曲遂成商旅游宦之歌。吴歌西曲,或是寄人篱下的女子所作,或是唱自歌伎之口,作者难考,但无疑反映了市民的色彩和情调。
吴歌西曲多表现男女情爱,往往表现得相当放荡,这是从前的民歌中所未尝有过的。如《子夜四时歌》中《秋歌》的第四首: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
再如:
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
此类歌谣中描摹旖旎风光、率真奔放之爱恋与软腻浪漫之情调,极富新鲜感和市民趣味,广受喜好。
吴歌西曲经由倡优艺妓、豪商富贾之口,传衍至社会各阶层,就有贵族采集和模拟这些艳歌。《南史·王俭传》云:“褚彦回弹琵琴,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梁书·羊侃传》云:“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最早大量地学习吴歌西曲,因而也最受正统贵族奚落的,却是下层文人鲍照和汤惠休。颜延之称汤惠休的诗是“委巷中歌谣耳”。起先是鲍照这样不避俚俗的下层文士,进而是在浮华空气中出生的“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终于,拟作“里巷歌谣”成了盛极一时的风气。及至梁武帝,将这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翻了个,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提倡。《唐书·乐志》载梁武帝曾令沈约拟《白纻舞歌诗》的歌辞而改题为《四时白纻歌》。而《白纻舞歌诗》的大意如《乐府解题》所说,是“盛称舞者之美,宜及芳时为乐”。这个时候,宫廷文学中已经透露出了浓厚的宫体的气息。宫体诗风在简文帝时出现,实际上是水到渠成。
市井流行歌曲的浮华风气同宫廷奢侈享乐汇合,首先,产生了音乐方面的变化。江南流行清商曲,清商曲以丝竹乐器为主,音声动人,被认为是“郑卫之音”,因此深得贵族的喜爱。梁裴子野的《宋略·乐志叙》描述宋以来的音乐歌舞云:“优杂子女,荡目淫心。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慢为环玮,会同飨觐,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在上班(疑脱一字)赐宠臣,群下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伤风败俗,莫不在此。”梁武帝宫中也有专门演唱吴歌西曲的女伎。《南史·徐勉传》载,梁普通年间,梁武帝挑选“后宫吴歌、西曲女妓各一部”赐予徐勉。歌曲有曲有辞,配合着“郑卫之音”的就是艳诗。对宫廷文艺说来,辞和曲的影响是同时发生的。因而梁代萧子显评价当时的艳诗体云:“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宫体诗多作于歌舞宴集之上,诗成之后交付歌伎演唱,其中有的是依声作辞,有的是由乐工乐伎配上曲谱,但都不出当时流行的清商曲。
其次,对吴歌西曲等市民文学的接受,使宫廷贵族逐渐偏离正统文学观念。当时有一些正统贵族如萧子显和裴子野维持着贵族的体面,对流行的艳歌持轻蔑的态度,但萧子显又不能不承认艳歌盛极一时的现状,只好说“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裴子野的《雕虫论》也说自宋以来,“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但简文帝萧纲站在贵游年少一边,倡导离经叛道的主情说,反对文学以经典为范本,他在《与湘东王书》中云:“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吟咏性情是有明显倾向的,《答新渝侯和诗书》云:“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情性”狭窄到了“艳情”,而“吟咏情性”本也不想“止乎礼义”,而是与“摈落六艺”互为因果的。这清楚说明宫廷贵族内部的分化和正统诗教在贵族中的衰落。
宫体诗的出现也有诗体自身发展的因素。六朝诗体,由玄言而山水而咏物。简文帝之前,诗歌描写对象大抵有天文、气象、动物、植物、器物等,至简文时代,王室士族奢侈淫逸,蓄妓养妾风气甚盛,女色声伎的享受成为门第世家的生活重心。于是,诗人文士咏物的兴趣与注意力,也转向集中于宫廷女子身上,由直接写酥软和横陈的女人进而写闺思和娈童,再写女人所用的物品来代替人,诸如接近肉体的绣袜、枕席卧具,以及其他器物。再由于女性复杂多样的容止情态,具有特殊美感与吸引力,诗人得以客观写实的态度,并以形似、细密、雕琢的手法,全力描绘女性内在与外在的各种怜爱情态,于是侧艳的宫体诗诞生了。
宫体诗是在永明体基础上出现的“新变”诗体,由永明体写自然山水转为写艳情,更注重形式的华美精巧。宫体诗作家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宫体诗人中坚徐陵也刻意求新,《南史》说“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传写成诵”。萧纲、萧绎也明确地反对“宗经”,反对以政治与伦理的标准约束文学,他们看重文学的美感与抒情。萧纲更主张全面新变,提倡“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萧绎也要求文学“绮彀纷披”、“情灵摇荡”。宫体诗的“新变”不仅指题材,也有辞藻、声律等内容。
宫体诗“新变”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摆脱了儒家传统观念的束缚,离经叛道,多以女性为描写对象。宫体诗人认为写女性具有美感,是有新变意味的好题材,因而大胆描绘女性容颜、体态、服饰及男女艳情,而提供了新的审美类型,拓展了诗歌题材。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继二谢以山水为主题的诗歌一变为描绘人物为主的“宫体”,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和革新精神。当然,宫体诗中女性是被观看与被描写的对象,依然表露出传统“男尊女卑”、“夫主妇从”的性别政治,在这种“宰制—统治—从属”的文化政治关系凝视下,宫体诗中“妇女”具有固定的形象特征:温柔、怯弱、谦卑、顺从等等。
宫体诗“新变”的第二个特征是在声律方面向前跨了一大步,因而在汉语诗体流变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我们先看宫体诗的体式流变。宫体诗的主要体裁是五言和七言,五言占绝对优势,七言尽管也是主要体裁,但它仅有五言诗的四分之一,其他句式在宫体诗中微乎其微。宫体诗之前,元嘉体以长篇为多,半数在十八句以上;永明体诗歌中,八到十六句的诗歌过半,短篇制作是大多数。但这种变短的趋势只是刚刚开始,长短篇之间的差距并不大,短篇的数量只比长篇略高一点,而二十句式的数量仍然很多,也是沈、谢的主要体裁。宫体诗中,十二句以内的作品占了压倒性优势,短篇制作中数量最多的是四句式和八句式。综合来看,五、七言中,使用频率由高到低的排序是四句式、八句式、六句式和十句式。参阅归青《南朝宫体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9-184页。这样一来,宫体诗在诗体发展过程中所占的位置一目了然。诗歌趋短有各种因素,既是对晋宋诗歌繁复铺张倾向的反拨,也是受到民歌影响的结果。吴歌西曲中五言四句较多,这对宫体诗人的创作有直接影响。
其次,对偶的大量使用也是宫体诗体式流变的重要方面。有学者通过数量统计发现,宫体诗中绝大部分作品是对偶诗,宫体诗人对对偶技巧是相当重视的。宫体诗人使用对偶相当频繁,对偶句在宫体诗中占很大比例。对宫体诗中对偶的数量分析,参看归青《南朝宫体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6-187页。词性相对是对偶能否成立的最基本条件,也就是做到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等等。进一步提升难度的话,就是在同一词性内部进一步分出若干小类,要求以小类相对,如天文对天文,地理对地理,这就是工对。还可以要求对句做到结构相对,如动宾对动宾、主谓对主谓,修饰对修饰,等等。检查宫体诗中的对偶句,以词性相对(宽对)和结构相对而言,宫体诗的偶句大体上都做到了。
按照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中的归类,工对可以具体分为十一类和若干门,只有同类同门的词相对才算工对。王力先生的分类主要以唐诗为依据,以此衡量宫体诗,也同样实用。现略举一些例证:
一、天文对。“何当照梁日,还作入山云。”(萧纲《采桑》)“玉阶风转急,长城雪应暗。”(庾信《夜听捣衣诗》)
二、花鸟对。“细萍重叠长,新花历乱开。”(萧纲《采桑》)“竹叶裁衣带,梅花奠酒盘。”(徐陵《春情》)
三、器物对。“月辉横射枕,灯光半隐床。”(萧纲《夜夜曲》)“奇香分细雾,石炭捣轻纨。”(徐陵《春情》)
四、衣饰对。“下床著珠珮,捉镜安花镊。”(萧纲《采桑》)“风住疑衫密,船小畏裾长。”(陈叔宝《采莲曲》)
五、形体对。“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庾信《王昭君》)“落花同泪脸,初月似愁眉。”(陈叔宝《有所思》)
六、宫室对。“一去葡萄观,长别披香宫。”(萧纲《明君辞》)“合殿生光彩,离宫起烟雾。”(庾肩吾《赋得横吹曲长安道》)
七、颜色对。“白石春泉满,黄金新埒开。”(庾信《咏画屏》)“杨柳条青楼上轻,梅花色白雪中明。”(江总《梅花落》)
八、人名对。“自作明君辞,还教绿珠舞。”(庾肩吾《石崇金谷妓》)“歌撩李都尉,果掷潘河阳。”(庾信《结客少年场行》)
九、地名对。“偃师虽北连,辕已南背。”(萧纲《伤离新体诗》)“龙城远,雁门寒。”(徐陵《长相思》二首之一)
十、数字对。“欲传千里意,不照十年悲。”(萧纲《华月》)“荡子十年别,罗衣双带长。”(刘孝绰《古意送沈宏》)
十一、方位对。“东西争赠玉,纵横来问家。”(萧纲《茱萸女》)“杏梁始东照,柘火未西驰。”(萧绎《树名诗》)
十二、重叠字对。“尘镜朝朝掩,寒衾夜夜空。”(萧绎《闺怨》)“袅袅河堤树,依依魏主营。”(徐陵《折杨柳》)
上面列举了一些宫体诗中的工对偶句,可以说,后来唐诗中的工对种类在宫体诗中都已出现,而且数量不少。当然,上举例子基本上都属于一句中只有一个字属对工整的一般工对。一句两字以上属对工整和全部成分属对工整的工对句,在宫体诗中也有不少,如:“但问愁多少,便知夜短长。”(萧纲《拟沈隐侯夜夜曲》)其中,“但”与“便”都是副词,“多少”和“短长”都是反义词,属工对,“愁”与“夜”不是工对。再如:“鱼游连北水,鹄作辽东鸣。”(萧绎《龟兆名诗》)“鱼”与“鹄”是花鸟对,“连北”与“辽东”是地名对,还包含着方位对,但“水”与“鸣”不是工对。完全工对的,如:“殿上图神女,宫里出佳人。”(萧纲《咏美人看画》)“殿”与“宫”是宫室对,“上”与“里”是方位对,“神女”与“佳人”是人物对。“梅新杂柳故,粉白映纶红”(庾肩吾《送别于建兴苑相逢》)这一联中既两句相对,又句中自对,“梅新”和“柳故”,“粉白”和“纶红”,都对得很工整。这样的句子每个成分属对工整,结构也一样,有些句子甚至做到字字工对,这类诗句在宫体诗中数量不少。
我们进而以意义为标准考察宫体诗的对偶。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指出:“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刘勰事实上取着两个标准。其中,言对、事对是以是否用典为标准,正对、反对是以两句意义是否相反为标准,都侧重对偶的意义。从宫体诗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的偶句都是言对和正对。上文所举的诗句绝大部分都是言对,即不用典故的。宫体诗是一种体物诗,作者描写对象时常常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展示,必然要大量使用正对的写法。如:
风生解刺浪,水深能捉船。(萧纲《棹歌行》)
歌声临画阁,舞袖出芳林。(庾肩吾《咏舞曲应令》)
愁多明月下,泪尽雁行前。(陈叔宝《有所思》)
这样的偶句用两句补足一层意思,在宫体诗中占着绝大多数的比例。
刘勰推崇事对与反对,就修辞设定的条件言,事对与反对的难度要大些。从这个角度看,宫体诗中也有一些写得比较成功的例子。先看事对:
本异摇舟咎,何关窃席疑。(萧纲《妾薄命篇》)
武昌识新种,官渡有残生。(陈叔宝《折杨柳》之一)
从所引例子可以看出,宫体诗人善于使用事对,常借助一些香艳的典故,给诗歌增添轻艳色彩。所用典故较浅显易懂,很少堆砌。当然,宫体诗的事对不占主导。再看反对:
迎来挟瑟易,送别但歌难。(萧纲《赋得当垆》)
向户疑新箔,登巢识故泥。(庾肩吾《咏檐燕》)
窈窕怀贞室,风流挟琴归。(江总《妇病行》)
反对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但宫体诗中反对的偶句并不多。当然,正对为多,反对为少,为诗歌对偶的普遍情形。
宫体诗诗体流变的第三个方面,是对诗歌声律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诗歌的声律体现在句、联、篇三个方面。律句分为严格律句和特殊律句。依据归青对萧纲、庾肩吾、萧绎、庾信、陈叔宝、徐陵、江总七位诗人二百六十八首诗歌的考察,严格律句数量约占总句数的百分之六十归青《南朝宫体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而据刘跃进统计,永明体主要成员王融、沈约、谢脁的严格律句,都未超过总诗句数的一半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第116页。。两相比较,显示出声律进步的迹象。而且,宫体诗中通篇或者几乎都由严格律句组成的作品时时可见。如萧纲《咏武陵王左右》:
顶分如两髻,簪长验上头。(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投杯如欲转,疑残已复留。(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宫体诗中的特殊律句并不多,且基本上是“平平仄平仄”格式。例如,“铜梁指斜谷”(萧纲《蜀国弦歌篇十韵》);“情来共相忆”(萧纲《临高台》);“倡家怨思妾”(徐陵《梅花落》);“当由好留客”(徐陵《奉和咏舞》)。特殊律句作为严格律句的变体,基本上是近体格律形成以后发展出来的格式,因而宫体诗等新变体很少遇到这种格式。
其次,考察律联的情况。声律论要求入律的两句必须平仄相对,构成一副律联。宫体诗中的律联并不少。如:
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庾信《昭君辞应诏》)
数镊经无乱,新浆纬易牵。(徐陵《中妇织流黄》)
上举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式的律联。再如:
不无夫婿马,空驻使君车。(萧纲《茱萸女》)
横波翻泻泪,束素反缄愁。(江总《七夕》)
这是“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的格式。宫体诗的律联当然不止这几种,但我们发现律联在诗联中的比例并不高,主要原因恐怕是宫体诗人的声律技巧还不够纯熟。
至于律联在诗歌中所占的比例,在七位主要宫体诗人(萧纲、庾肩吾、萧绎、庾信、陈叔宝、徐陵、江总)的诗歌中,律联超过全篇联数一半以上的诗歌接近三分之一,只有一联非律联和全篇都是律联的诗歌几乎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宫体诗中相邻律联的联结方式,首先是对式法,即按照平仄相对的原则来联结律联的方式,或者说某一种律联的反复使用。如庾信《和咏舞》:
顿履随疏节,低鬟逐上声。(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步转行初进,衫飘曲未成。(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宫体诗中这种律联的联结法最多,可以看做对永明体律联联结方式的继承。
第二种联结方式是黏式法,这是指相邻律联之间按照同声相黏的原则互相联结的方式。即前一联的下句和后一联的上句中第二字和第四字必须同声。如萧纲《娈童》:
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黏式法既保留了诗歌平仄相对的特点,又避免了单调重复的弊病。但其在宫体诗中的使用率比对式法低得多,说明宫体诗人虽注意到这种联结法的长处,并作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和实践,但仍不占主导。宫体诗中出现了一些完全或基本(三联以上的作品只有一联不合律)合律的齐梁体格律诗,虽然数量比例只能以凤毛麟角加以形容,但也显示出诗歌格律化程度的提高。宫体诗中律联的组合方式中的黏式律诗有两种格式:一是用平起仄收,以“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黏合“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另一种是仄起仄收,以“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黏合“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而成。此外也有将对式法和黏式法交替使用的混合律诗出现。
总结起来,宫体诗的声律水平在永明体的基础上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律句增加,但在联结成篇上并无大的突破,其中关键在于诗歌中的律联尚少,还不能完成永明体向近体诗的飞跃。
不过,综合宫体诗中的对偶、平仄因素,我们看到部分宫体诗已非常接近定型的五律、五七绝。如萧纲的《和湘东王横吹曲·洛阳道》:
洛阳佳丽所,大道满春光。游童初挟弹,蚕妾始提筐。
金鞍照龙马,罗袂拂春桑。玉车争晚入,潘果溢高箱。
诗歌对仗工整,中间四句与五律已很接近,是五律即将成熟的先声。再如他的《晚日后堂诗》:
幔阴通碧砌,日影度城隅。岸柳垂长叶,窗桃落细跗。
花留蛱蝶粉,竹翳蜻蜓珠。赏心无与共,染翰独蜘橱。
这首诗已具备了五律律诗的雏形,诗的前半部分完全符合近体诗的格律。萧纲能有意识地做到声韵协调,平仄相对,而且对仗精整。这说明他对于声律的掌握已趋向自觉,尤其是他的《夜望单飞雁》:“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这种七言四句的诗歌形式,为唐代七言绝句的成熟打下了基础,这种形式在齐梁尚不多见,萧纲的创作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而庾肩吾最讲究诗歌格律工整和谐、雕章琢句。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曰:“诗之佳者,在声色臭味之俱备,庾肩吾是也。”陈祚明也评论说:“庾子慎诗,当其兴会符合,音节顿谐唐人,构思百出,差能津逮。”(《采菽堂古诗选》)比如他的《和徐主簿望月》:
楼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照雪光偏冷,临花色转春。
星流时入晕,桂长欲侵轮。愿以重光曲,承君歌扇尘。
这首诗声律上已接近完整的五言律诗,是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重要标志。徐陵从小得以进出萧纲门下,是宫体诗派的中坚人物,他的《乌栖曲》二首:
卓女红妆期此夜,胡姬沽酒谁论价?风流荀令好儿郎,偏能傅粉复薰香。
绣帐罗帷隐灯烛,一夜千年犹不足。唯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
这两首均为七言四句,用韵平仄相间,酷似初唐七绝。
作为一种新变体诗歌,宫体诗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典的,而且有自己的特点。宫体诗人对元嘉诗乃至永明诗的风格体制有所不满,他们面对元嘉体堆砌典故的弊病,要求诗歌“不雅不俗”,在用典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宫体诗人仍较重视用典,但用典比例比较低,而且绝大部分的五言四句式诗歌是不用典的。至于用典的密度,宫体诗人改变了元嘉体那种叠床架屋的用典方式,为诗歌的流畅自然创造了条件。我们注意到,宫体诗中的用典大部分是浅近易懂的和较熟悉的典故,有助于风格的典雅含蓄。而且,宫体诗人追求“用典不使人觉”,“不啻自其口出”,就是要求从诗意出发,对典故适当剪裁融化为我所用,而且还要巧妙化用前人诗意、句意,从而使典故与诗歌意境内容融合为一。
至于语言风格方面,宫体诗人讲求诗歌语言的平易明快,反对过于书面化和深奥艰涩。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萧纲的《春江曲》:“客行只念路,相争度京口。谁知堤上人,拭泪空摇手。”朴素如同口语,也很精练。又如他朴素明朗,本色天然的《乌栖曲四首》其一:“芙蓉作船丝作笮,北斗横天月将落。采桑渡头碍黄河,郎今欲渡畏风波。”颇具民歌风味,而又奇丽精工。总之,宫体诗在对元嘉体和乐府民歌风格综合和改造基础上形成了平易流畅、优美精致的风格,这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魏晋古诗淡泊古朴的语言风格在南朝以后为一种风华流丽的语言风格所代替,其中宫体诗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宫体诗的词汇是适应它所表现的内容的,带有宫廷的气息和脂粉气。
总结起来,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一些特点,继续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为近体诗的出现做了准备。从篇幅上看,宫体诗通常较短,并逐步凝聚为以八句、十句为主的形式。同时,四句的形式也被普遍采用,简文帝和庾信等人都有很不错的绝句诗。他们之前,绝句主要出现在六朝的乐府民歌中。从句式来看,魏晋诗歌中的许多虚词和散文句式被剔除,语言更加凝练而富于跳跃性,这是对仗日趋工稳和精巧的结果,也是新体诗声律实验的结果。
·下编章节目录·〔内容恕未收录〕
下编 诗人流变
第一章 诗人群体的变迁
第一节 三曹七子诗群的出现
第二节 竹林七贤的承继与变异
第三节 二十四友的因袭
第四节 竞陵八友
第二章 诗人生命意识之演化
第一节 建安文人慷慨的生命情怀
第二节 正始名士的生命焦灼与逃遁
第三节 晋代诗人的生命意识
第四节 陶渊明的生命思考
第五节 南朝诗人的生命意识
第六节 佛教对南朝诗人生命意识的影响
第三章 诗人人格模式之变
第一节 邺下与竹林诗人群体的人格模式
第二节 西晋诗人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
第三节 东晋诗人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人格模式
第四节 齐梁士族诗人“无奈须眉不丈夫”的委琐人格。
〔共八页〕
1
2
3
4
5
6
7
8
上一页 返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