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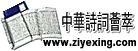 |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 |
|
文/朱光宝 海阔中文网网站整理收录·仅供参考
上编·诗体流变
导 论
一
诗,具有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诗,是人类心灵的深切呼唤。
诗是一条流经人类每个角落永不枯竭的清清小河。
诗是不受时空条件限制的。那是因为由诗所传达出的人的美好情感是不受时空条件限制的。诗,可以越过沧桑岁月,到达地老天荒。
诗是整体意义上的美,是春风沉醉的美。诗是美的极致,因为诗具有巨大的艺术容量和广阔的想象空间。
诗情和诗意充满着美好的善意。诗,从来都是引人向善的。诗过去不会今后永远也不会让人向恶。
诗可以达成各个地域的人们心灵之间的牵手。
所以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要内容是《诗学》,他指出诗是“创造的科学”;所以康德提出诗美“是道德的标志”,而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古希腊有《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那样的荷马史诗,古代中国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样的诗,我国藏民族也有史诗《格萨尔王传》,这些都无一不在证明着诗的普世价值和恒久美感。
二十世纪中,诗更是把人类生活提升到新的高度。海德格尔说:“人类应当诗意地栖居在这片星球上。”诗在当代不仅具有普世价值,更成为人类生活新的标尺。
二
诗在中国具有更加崇高更加特殊的地位。在中国,诗从有史之初就受到格外的尊崇。中国是诗的国度。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拥有像中国这样数量巨大的诗歌和众多的诗人。
诗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孔子是最早发现诗的巨大价值和崇高地位的人,他是最早、最杰出的诗学家。他反复阅读《诗三百》,他又重新修订和编辑《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然而《论语》中孔子已多处说过“诗三百”的话,《墨子·公孟篇》中也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话。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这一年到鲁,鲁国为他表演的《诗》从名称到顺序都与今天《诗经》基本相同,而孔子这年只有十岁。由此可见,孔子当时《诗》已成集。但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子罕》中记有“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史记》关于孔子删《诗》之说并非全无根据。因此笔者认为,孔子在读诗传诗过程中也整理修订过《诗》。人们感叹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其实,他读《诗》何尝不也是韦编三绝。
孔子高度重视诗。他在《论语·季氏》中说:“不学诗,无以言。”长时期以来,人们总是从修辞学角度理解孔子这句话,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讲话,例如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就把“不学诗,无以言”译成“不学诗就不会说话”。其实孔子在这里说的是“不学诗就不能讲话”,是关于话语权、发言权的问题。可见孔子对诗的重视。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强调了诗的综合性、全方位的意义和价值,虽然我并不赞成他让诗为政治教化服务的观点。他在《论语·泰伯》中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这三个大的阶段构成人的心智成长、精神发育的全过程,而诗则是宇宙观养成的第一步。“兴于诗”是指诗让人振奋,让人激动,让人富于激情地生活。诗召唤人们生活的激情、生命的激情。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再经过“礼”的熏陶,使人合乎社会规则地生活,合理地站立在社会群体之中。最后完成的阶段是“乐”,乐又是富于浓厚感情色彩的,但这时的感性化却是和理性化高度统一的,是一种具有理性元素,与理性水乳交融的感性。是否定之否定的完成式。
“诗──礼──乐”这条人生成长的轨迹,诗在开端,在起点。
诗是重感情的,是表达感情的,是用感情来打动人、感化人的。孔子也正是从“诗──礼──乐”这条精神成长道路上走过来的。他是有着博大精深思想的哲人,他又是满怀充沛感情的诗人。他是有性情的,是有激情的,他就是“兴于诗”的。真正了不起的人,也就是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人,一定是满怀激情而又一腔深情的。孔子就是这样。我们读《论语》,里面处处是饱含感情的句子,完全没有那种板起脸孔的态度。孔子是我国最早、最有成就的教师和文化传播者,他实行的“师道”,不是讲求尊严,而是热情洋溢、感慨万端,并用热情和感慨去感染学生,让他们从感情上去热爱知识,进而对知识产生理解、尊重之情。这是教育学最重要的使命和方法,这是富于诗意的教学法。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兴于诗”的深刻本质和具体运用。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录了孔子一生中最后唱的一首歌。这是他七十三岁临终前唱的歌,也是他把诗与乐、把感性和理性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歌词共三句:
“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译:泰山崩塌了!天柱摧折了!哲人离去了!〕
这是孔子用诗歌表达的人生最后感慨。七天之后,他去世了。
斯人已逝,但他强调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留给我们极其深刻的启发:
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情感的丰富而不是情感的枯竭,是情感的敏锐而不是情感的麻木,是情感的充盈流动而不是情感的萎缩凝滞,是情怀的自然天成而不是情怀的矫揉造作(参看鲍鹏山《说孔子》,上海高教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
孔子是我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影响力最深巨、最持久的华夏文化传播者和创立者,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中国人。孔子以及他所创立的学说早已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内核和心灵印记。“自孔子之前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之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这是柳诒徵先生作出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评判。朱熹甚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唐子西尝于邮亭梁间见此语。”唐子西名庚,北宋诗人,其《唐子西文录》中记曰:“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不知何人诗也。”可见为无名氏所作。后世多系之于朱熹名下。
随着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全社会的至尊地位的确立和持续不断的强化,孔子的诗学上升为诗教。作为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大精神支柱,成为道德伦理体系、政治理论体系和社会行为规范的组成部分。
中国对诗和诗学的重视,诗和诗学在中国所体现出的极其崇高的价值,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三
在这样的诗的国度中,诗歌精神与诗人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诗歌品格与诗人品格紧密结合在一起。回望历史,先秦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诗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体现出极高的人格尊严,无论公德私德,他们都有自己坚守的价值尺度和道德尺度,并且一以贯之,甚至以生命殉之。屈原就是这样的诗人。他的诗品也正是他的人品。“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这就是孔子说的志士仁人,孟子说的大丈夫。屈原的身后,站立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雕像:“唐雎不辱使命”、“赵氏孤儿”、“信陵君窃符救赵”等等,为中国诗人确立了一个精神高度和人生高度的坐标,具有超越历史的感召力。
《诗经》之后,出现了屈原,他吸收民歌营养,另创新体,成为“骚体诗”的创立者。他是中国诗史上文人创作从民间创作中分流出来的第一个作家,是第一个伟大诗人,是中国文人诗的第一座高峰。无论从诗人之变还是从诗体之变上看,屈原都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变局。
汉代是中华民族的定型期,是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形态最终确立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繁荣而又稳定的封建王朝。至汉武帝时,国运空前昌盛,日丽中天,这样的社会现实很容易在人们心理上培育出奋发向上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影响到文学艺术,便产生了一种阳刚崇高、义尚光大的审美倾向。在建筑艺术、雕刻艺术、绘画艺术和文学艺术上都是如此,都具有雄浑博大的气魄、粗犷豪放的风格和深沉稳定的力度。诗人文士满怀参与生活的激情,以奔放雄健的笔力,描写大好河山,作品中洋溢着按捺不住的赞叹和欣喜之情。这一点如李泽厚所言:“在一个琳琅满目、五色斑斓的形象系列中,强有力地表现出人对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的征服主题。”(李泽厚《美的历程》)面对着大汉帝国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局面,诗人文士对美丽、富饶、繁荣、昌盛、先进、强大的祖国尽情讴歌礼赞。在诗体上,汉代人继续着屈原骚体诗的变化之路而更进一步,创变出形式更自由的诗体──汉赋。刘邦是楚人,汉文化主要传承的是楚风,同时融入儒、道文化元素。本真狂放、情感热烈、心胸开阔、气派雄沉、资质悲壮是两汉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集中体现在司马迁、李固、陈蕃、范滂等士人身上。司马迁的人生追求和伟大人格,深刻影响着汉代诗人。李固、陈蕃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以澄清天下为志,是知识分子群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一代,其慷慨赴死的壮烈,为正直知识分子提供了风骨上的楷模,也为汉代乃至三国时代诗人精神之变播种下内因。
魏晋时代是中国诗史上尤为显著的变革期,向我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心灵世界和人格世界。官方意识形态向心力的涣散,带来了文化生态的多元,刺激了“人的觉醒”。于是,一种“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不理会冠冕堂皇的教条礼法,只管放任性情,自由自在,被称为“魏晋风流”的人生范式出现了。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渊明等。魏晋诗人追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现出高逸的内在人格。他们纵情享乐,又满怀诗心哲意,潇洒不群,超然自得,无为而又无不为,药、酒、诗、乐,谈玄论道,山水景色……与他们相伴,如影随形。魏晋诗人超凡脱俗的高贵气派和绰约风姿,为那个时代留下了“遥远的绝响”。
这种状况,对那个时代的诗人之变、诗风之变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南朝文化是魏晋文化的延伸,尤其是东晋文化的延伸。东晋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另一番面目,它是第一个只拥有江左之地的汉族王朝,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衣冠南渡”。黄河流域和中原大地成了北方少数民族铁骑逐鹿的场所。大批王室、贵族和士人渡过长江,在江左安身立命。东晋,是中华文明重心第一次从黄河流域迁徙到长江流域的时期。
地域范围的锐减使得东晋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面貌空前狭小,这是制约和影响东晋诗歌的最根本因素。又兼西晋后期之内外战乱连绵不已,大批文士死于非命,诗人队伍元气大伤,过江之时,诗人已寥寥无几。因此,东晋诗歌总体上呈现出“小”的特征,诗人队伍规模小,诗坛气象格局也小。自然,诗歌成就也较小,没有出现建安那样的诗歌高潮,也没有出现正始、太康时的诗歌景象。
东晋诗歌整体上的另一特征是“弱”。东晋一朝,偏安江左,以守江自保为满足,毫无朝政之振起和民气之发扬的志向与举措。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晋元帝,早已怀有“据守江东”的打算。他曾对作为吴人的骠骑将军顾荣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的话(《世说新语·言语》),似乎怀有内疚之情和兴亡之思,其实这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和姿态。他这番试探性的话语,得到顾荣“王者以天下为家,……陛下勿以迁都为念”的回答后,即安下心来。文人士大夫也莫不如此,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首辅大臣王导,曾有“努力王室,克复神州”的豪言(《世说新语·言语》),但这种“黍离之痛”很快就化作一缕淡淡的怅惘轻烟。他执政二十余年,未见任何“克复”举动。作为东晋第二代士大夫中领袖人物的王羲之,更是“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在这样的世风人情之下,东晋诗歌缺乏遒劲的风力、崇高的精神和慷慨的情调,体质和文气大大弱于建安、正始是必然的。
南朝正是承继了东晋诗风的余绪,南朝诗的基本面也正是小、弱。到了梁陈之际,宫体诗勃兴,诗歌题材、气象更为狭小,被陈子昂斥为“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与魏晋南北朝相连接的,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高峰同时也是中国“诗歌王朝”的高峰──唐朝与唐诗。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王朝之中最具人的气象的朝代,是真正的民富国强的盛世。唐朝也是中国文化史、中国诗歌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篇章。开放、多元、激情、理性而又浪漫,南北文化交流密切,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伴随着“胡商”的云集,“胡姬”、“胡酒”、“胡乐”、“胡服”也成为一时之风尚。这是一个空前的古今中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为国建功立业的荣誉感、成就感和英雄主义,以及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激情和想象,充溢在社会氛围之中。
大唐气象的典型代表是唐诗。唐诗多姿多彩,气象万千。有李白式的青春张扬,有杜甫式的沉郁顿挫,或如边塞诗那样的豪迈壮丽、虎虎生风,或如田园诗那样的优美宁静、意境深远,有《登幽州台歌》那样的胸怀高蹈、独领风骚,有《春江花月夜》那样的优美明快、寥廓神秘,还有李商隐诗的情意绵绵、一唱三叹……这是个诗人最多、诗作最多、成就最大的诗歌时代。唐诗从各个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高度,展现了人的精神的自由和心灵世界的丰富。
魏晋南北朝正处在唐诗兴起的前奏期,它又是《诗》《骚》以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大变化转折期。它是秦汉与唐朝之间的“夹缝时代”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在中国诗史上,它也是《诗》《骚》与唐诗之间的夹缝时代。魏晋南北朝诗上承《诗》《骚》的影响和演变而来,下则过渡和开启了唐诗。这是中国诗史上不容忽视的关键时期。我们关注这个时期,关注这个时代的诗歌变迁,关注这个时代诗人群体的变迁、诗人人格的变迁和诗人生命意识之演化。
四
变化是事物的普遍规律。正如魏晋南北朝的诗人之变一样,这个时代的诗歌艺术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陆机《文赋》指出:“体有万殊,物无一量。”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魏晋南北朝诗歌正是“为体屡迁”值得关注的一个枢纽期。
关于诗歌体式之变,一千七百年前的晋人挚虞(?—311)第一次作出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讨论:
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浻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
──《文章流别论》,此据《艺术类聚·五十六》转引
挚虞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诗体演变的脉络。中国诗的源头是《诗三百》,而《诗三百》中诗的体裁句式绝大多数是四言。从语言的角度看,四言诗具有整齐稳重的特点,在变化上也显得相对简单,这种简单性正与人类早期语言表达的简单朴素相一致。从音乐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早期人类的乐感,无论是旋律还是节奏,都呈现出简单和整齐。鲁迅在探讨文学起源时,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他在《门外文谈》中说,劳动时的众人协同用力催生了劳动号子。所以他说自己是“杭哟、杭哟”派。《诗三百》中的四言诗正具有这种“一句两个节拍”的简单稳定的节奏特点。
学界论《诗经》之体,又常有“雅”“颂”“风”“南”四体之说。雅即小雅、大雅,颂即商、周、鲁三颂,风即十三国风,南即周南、召南(顾炎武《日知录》、梁启超《释四诗名义》)。颂是原始的舞曲祭歌,雅是西周土乐,风是黄河流域各地的土乐,南是长江流域的土乐。雅、颂起源较早,至迟在西周前期和中期即已存在。风诗是晚出的新声,大约在西周末期兴起,有《桧风》可证。南诗的出现大约在平王东迁之后,因为长江流域的渐渐开发是公元前8世纪之后的事。二南之中,也明显可见没有西周诗歌。孔子在《论语》中再三称道二南,如: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
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女为周南召南已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可见后来者居上,“南诗”是“四体”中最进步的。但此种论体,着眼于音乐种类的划分,与我们论及的体式之变已无关涉。
《诗经》之后,诗歌逐步发展,诗体也逐渐变化。挚虞论体,论及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诗经》四言之后,即论三言。但《诗经》之后,应是战国时期的楚辞(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对屈原及其作品均提出疑问,但仅属“大胆假设”,尚未做到“小心求证”)。为何挚虞不论楚辞体而直接讨论汉代乐府中的三言体呢?推想其原因,或许挚虞认为“辞”不能称作“诗”。后世学者也多有此意,如朱东润先生《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就将屈原作品列为“辞赋”而与“诗歌”区别。楚辞句式变化大,六言、七言、八言交错,甚至还有九字句,例如《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可见屈原作品属于长句长篇一类的作品,句式变化大,但我认为仍应归入“诗”。这是一种体式特殊的诗。楚人敬重鬼神,祭祀活动繁多,活动中歌唱不已,故而形成了“楚辞”这种特殊形态的诗──长句长篇的作品。这与黄河流域的诗歌形态有较大区别。应该说,楚文化表现在诗歌上,它朝前迈出的步子很大,从内容和形式上看都是一种更先进的诗歌。但是,当时文化的主流是黄河文化,诗歌形态从四言径直跳到六言、七言或八言、九言,难以被主流文化所认同和接受。这也揭示出诗体发展不能是“突进”式的,而只能是“渐进”式的。在中国诗史上,诗体由四言循序渐进而至五言,再进至七言,最后以五言、七言定格为诗歌的基本体式。这也体现了诗体发展的规律。
楚辞作为诗歌,犹如炫目一现的昙花。
然而正因为楚辞体诗歌具有超前性,它在后来诗的发展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如汉初项羽之七言四句的《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又如刘邦之七言三句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过了七十年,到了汉武帝时,又出现了武帝的《秋风辞》、李陵的《别苏武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和刘细君的《乌孙公主歌》。如《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楚辞体诗歌的长句形式已经逐渐趋向于七言,而它的长篇形式则朝着短小方向发展。楚辞体诗歌正是后世七言诗的滥觞。
《诗经》之后,诗体发展的正格是五言诗。三言体和杂言体则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变格。
三言诗以三字一句作为意义表达单位,显得过于短小,难以成立,正如二言一句的诗也无法成立一样。早期曾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样的诗句(《吴越春秋》),后来也两两归并而成四字句:“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三言句在《诗经》中数量很少,可见它在传情达意上无法与四言句抗衡。楚辞中的六字句多由两个三字句归并而成,七字句也是“三兮三”这样的特点,即两个三字句中间联结一个“兮”字。汉代郊祀祝颂之辞用了不少三言。由于其节奏短促有力,便于记颂,于是训诫之辞和民间谣谚也常用三言,但它用于艺术表达的回旋余地小,不易抒情,于是魏晋之时便已式微。也有极少量的三言诗写得十分成功,如魏末晋初诗人傅玄的《杂言诗》:
“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
全诗仅寥寥十二个字,把思妇在等待时的那种专注和痴迷之情描写得惟妙惟肖,真让人读后顿生“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慨叹了。这样的佳作,是三言诗中的凤毛麟角。
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中间还经历了杂言体的过渡阶段。杂言体的诗包含了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甚至还有二字一句和一字一句的。汉乐府诗有很多杂言诗作品,如《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只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又如《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些诗中,各体杂陈,长短随意,整散不拘,二、三、四、五、六、七言的诗句都有,是典型的杂言体。汉乐府多用杂言是由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决定的。乐府诗宣泄的是直露而激烈的思想感情,在中国诗史上是一次情感表露的大解放──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征夫弃妇的生离死别,痴男怨女的欢肠热泪,这些都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这样的思想内容当然只能用“杂言体”来表达。像《上邪》诗中那种犹如山洪暴发般的感情,怎能采用固定的章法和句式呢?一个爱情遭受挫折之后更加渴求爱情的女子,她呼天抢地般的呐喊,当然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四言诗之后出现的杂言体是一种新体诗,集中体现在汉乐府的《铙歌十八拍》中,包括《有所思》《上邪》在内的这十八首诗全是杂言,可谓自成一格。杂言相对于整齐的诗歌句式,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如果说汉乐府诗的作者完全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写杂言体的诗,并非有意识地创造新诗体的话,那么到了南朝刘宋时的鲍照和盛唐时的李白那里,他们则是自觉追求一种特殊的文学效果,在“歌行体”的诗中,把杂言的妙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是在杂言诗这一过渡期之中,孕育出了新型的诗体──五言诗。
前文所引挚虞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五言诗的最早形态是以一句两句杂在四言诗之中出现的。所指就是《诗经·召南·行露》,该诗如下: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这首诗共三章,首章三句,全是四言,二、三章每章六句,都是前四句五言,后两句四言。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诗经·小雅·北山》之中。但是,整部《诗经》中没有一首通篇五言的作品。这说明迄于春秋时期,只有零星的五言诗句,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篇。
晚于挚虞的南朝著名学者刘勰,同样高度关注五言诗起源,他指出:“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刘勰也是先考察《诗经》,找到的五言诗句的例子正与挚虞相同。但他接下来却以《沧浪》作为“全曲”,将其视作完整的五言诗篇。《沧浪》一诗见于两书,一为《楚辞·渔父》,一为《孟子·离娄》,《渔父》的真伪,后世争论很大,可不论。以《孟子》所引为据,则《沧浪》当产生于战国时代。其辞如下: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诗的一、三句都是六言,对此,刘勰认为其中的兮字“乃语助余声”,“无益文义”,故欲删去,从而视作五言。我们认为,汉字一字一音,字字独立,不能视“语助”为无物。《诗经》中有许多“语助”一类的虚字,如“薄言采之”的“薄言”,怎能删去?况且“兮”字在楚声诗歌中关系到体格特征,不可忽视,更不能删削。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即《汉书》中的《郊祀歌·天门》,其诗曰:
幡比翄回集,贰双飞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华燿以宣明。假清风轧忽,激长至重觞。
读后茫然,不知所云。再检王先谦《汉书补注》,发现原诗应是:
幡比翄兮回集,贰双飞兮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华燿以宣明。假清风兮轧忽,激长至兮重觞。
可见删削兮字以成五言,将乖违辞意,全不可通。
到了秦代,也没有出现完整的五言诗篇。秦代甚至没有任何诗歌作品流传下来。秦朝存世极为短暂,仅十四年,犹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苍穹。但是,秦王朝连年征伐,徭役繁苛,人民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形下,人民自会唱出心声,然而想必数量不会太少的民间歌谣却一首也没有流传下来,这是秦始皇和李斯实行“燔灭文章”的文化灭绝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到了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时,引用了三国末期吴人杨泉《物理论》中的一首民谣,其辞曰: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拄。
这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诗。它写的是秦朝征发大批民工修筑长城,百姓死亡无数的事。但它不是秦朝的作品,郦道元只是引用,并没有也不可能说明杨泉《物理论》中这首《长城谣》五言诗的来历和出处。比杨泉早数十年的建安诗人陈琳,有一首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的句子,这应该是《长城谣》五言诗的来源。杨泉诗正是删改陈琳诗而成。
汉初七十余年间,有戚夫人《舂歌》、李延年《北方有佳人》等作品,其中五言诗句明显增多,但仍不是全篇五言。直到汉武帝末期,才出现了民歌五言诗。《汉书·贡禹传》中记载:
何以孝悌为?多财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
到了汉成帝时,五言民歌渐渐多了起来: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汉书·尹赏传》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花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
民间文学总是新的文学,也是文学中新体式的源泉。它们犹如深山清泉,石涧春水,潺潺流来,静静地、无穷无已地赋予各个时代文学以新的生命。
在民间五言诗的滋养之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产生。东汉班固《咏史诗》楬橥之后,经张衡、蔡邕、秦嘉的不断发展而到《古诗十九首》,五言诗体式才完全成熟和定型
── 一个“五言腾踊”的诗歌时代来临了。
诗体变化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七言诗的出现与定型。
五言诗之后,诗体发展的正格是七言诗,六言诗则是这一发展进程中的变格。由此可见诗歌体式之变也与其他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充满了复杂性。
六言诗句在《诗经》《楚辞》中已出现,而尤以《楚辞》中为多。这一现象正如刘勰所言:“六言七言,杂出诗骚。”(《文心雕龙·明诗》)《离骚》中的多数诗句是六言、七言。汉代五言诗出现之后,至汉末开始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篇,如孔融的三首《六言诗》:
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其二〕
这是今天见到的诗歌史上最早的完整的六言诗,具有开创性意义。与孔融同时代但比他晚二十多年的曹丕,也写有六言诗,如《令诗》和《黎阳作诗》(“奉辞讨罪遐征”)。此后,六言诗时有诗人创作,零星出现。如南北朝集大成的诗人庾信有《怨歌行》:
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回头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
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为君能歌此曲,不觉心随断弦。
这是极为成熟的著名六言作品。即使到了诗体句式已经定型为五言、七言的唐代以及以后各个朝代,六言诗创作也不绝如缕。如盛唐王维的《田园乐之六》:
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归,莺啼山客犹眠。
到了北宋,王安石写下了“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题西太一宫壁》)这样的六言诗,南宋陆游有《感事六言》,其中有最能体现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的诗句:“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成丹”。到了现代,毛泽东写出了气势恢弘、大声镗鞳的六言诗《赠彭德怀》:
山高林密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跃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六言诗领域里奏出的最强音。
五言诗之后诗体变迁的主流方向是七言诗。自《诗经》《离骚》中的七言诗句之后,汉代的楚声歌在句式上已是完整的七言诗,只不过句中带有典型的楚风虚词“兮”字,如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和刘彻的《秋风辞》等等。到汉武帝时,出现了一首很特别的诗──《柏梁台诗》。据《东方朔别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于是联句而成《柏梁台诗》。全诗共二十六句,句句不带“兮”字,已是标准的七言句式。但顾炎武根据《史记》《汉书》的纪传年表,辨此诗的年代、官人皆相抵牾,定为后世依托之作。东汉时,与班固、傅毅同时的崔骃,写有一首七言诗:
鸾鸟高翔时来仪,应制归德合望规,啄食楝食饮华池。
全诗只有三句,虽无楚辞遗迹,但又欠完整。到了东汉中后期,张衡写出《四愁诗》(“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仍然在四章的每章首句夹有“兮”字。直到建安末期的公元220年前后,曹丕写出了中国诗史上最早、最成熟的完整七言诗《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一首创作于一千八百年前的文人乐府七言诗,今天读起来仍明白如话,而它又具有“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的艺术感染力(王夫之《姜斋诗话》),它音调和婉,“开千古妙境”(胡应麟《诗薮》),实在难得。《燕歌行》使七言诗从此登上诗坛,并占据重要地位。到了唐代,七言诗后来居上,成为格律诗的两种基本诗体之一。
五
历时三百八十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历史发生大转折的时期,又是一个思想发生大变化的时期。文学思想在这一时期显现出不同于此前也不同于此后的独有而鲜明的特征。
公元196年,充满征伐动荡的建安时代开始。中国进入新一轮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转折期。曹操经过南征北讨,力挫群雄,最终成为黄河流域和中原大地的霸主。汉献帝建安时期的二十五年间,曹操是全国范围内真正的发号施令者。至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建立魏国,献帝退位,汉朝终结,继而刘备帝蜀、孙权帝吴,鼎足而三的历史局面形成。到公元265年,魏亡,西晋建立,这同样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北方五个少数民族战乱不已,史称“五胡乱华”。西晋五十年后又亡,东晋渡江而立。中原大地经历了少数民族政权频繁更迭的“五胡十六国”的大动荡。南朝继东晋之后,也是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你争我夺,继相更迭。至公元589年隋朝统一,这一分化、割据的时代才告结束。
这个大转变的历史时代,对思想文化、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巨大的影响。对于诗歌而言,最突出的特征是逐步淡化了它与政治及教化的关系。
自周秦两汉以来,我国的思想传统中形成了两个基本元素──儒家与道家。儒家对于文学诗歌的态度是将其纳入政治教化的轨道,使之承担起工具性的使命。这样的态度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体现得非常鲜明,他有一段极其经典的话语:
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毫无疑问,这段话强调了对诗歌的事功性要求。汉儒《诗大序》出现之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思想更为明确,对诗歌工具性的要求更为强烈。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不同,他们对于文学诗歌的态度和影响是让其回归于人的自身,让诗歌回归人的心灵。以老庄学说为核心的玄学,在魏晋时得以创立,成为最具系统性和影响力的哲学体系。李泽厚、德里达等中外学者近年来提出“中国有思想无哲学”的观点,理由是中国“哲学”总是与现实伦常政治联系紧密,没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那样的纯思辨性。但笔者认为,玄学抽象思辨程度在我国古代各种思想学说中是最高的,而它与伦常政治的联系却是最弱的,因此它与哲学一词(philosophy)的含义至少是最接近的。(李泽厚观点可参见其《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及《论语今读》,前者为三联书店2003年版,后者为三联书店2004年版。)玄学看重人的认知能力、心灵自由和精神境界。文章是人情性的风标,是人精神上的律吕。玄学第一次打开了作家的灵魂之锁,使诗歌成为心灵的倾诉和情感的宣泄。魏晋时期的文学汇成蓬勃的运动,可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序》),在创作上出现了曹操、曹植、王粲、刘祯、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大诗人,在理论上也涌现出曹丕、陆机、钟嵘、刘勰、萧纲、萧绎、萧统那样的大理论家(其中尤以刘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最为夺目)。这些大诗人、大理论家为后世留下了永不泯灭的心声,为文学储备了取之不尽的宝藏,找一找时代原因,我们会看到思想大变化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
从建安开始,诗歌创作的鲜明特征就是摆脱“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影响,完全用于抒一己之情怀,正如刘勰所言:“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人完全把“以诗抒情”作为内心生活的需要。即使像曹操这样的大政治家,在其诗中也找不到“教化说”的痕迹,读“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这样的诗句,让人感受到的是曹操政治家情怀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出于教化的写作动机。这样的诗句,与王粲“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七哀诗》)抒发的感情并无二致,他们都沉浸在那种强烈的、带着时代深深印记的悲凉慷慨情思之中,“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正是这种情思不得不发的证明。
两晋玄风的劲吹,使诗歌离政治教化的距离更远。此时的诗人,从父辈的军旅情怀之中摆脱出来,进入谈座。此时的诗,从抒发强烈的情思,转入冷静的哲理思索,谈座的潇洒风流代替了马上的慷慨悲歌。从慷慨到安详,从激动到沉思,唯一没变的是“诗为心声”。在中国文学史上,那些真实抒发人生遭际心灵感受的种种体验,自然流露作者高洁情怀的作品,往往成了熏陶和铸就民族高尚情操和优秀品格的文化瑰宝;而那些标榜政教的作品,却常常味同嚼蜡,甚或充满思想糟粕,失去教化作用。正是抒发个人情怀之作,达成了教化目的,客观上实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到了南朝,诗歌的抒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形式美的表现,从对偶、用典、辞采的讲究,到永明声律的发现,形式美的有意追求达到了高峰。这是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大转变,它的意义在于自觉地张扬文学本身的艺术特质,文学已完全醉心于自身,属意于形式的美的追求。由抒情而玄思,由玄思而到抒情与形式美的探求并重,诗与文学的发展处处反映着个人情性抒发的本然之义,由玄学思潮发展起来的重内心、重个性、重气质的思想,渗透到诗歌创作之中,由此形成魏晋南北朝这一“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以降,文士发现了自己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并且用诗歌创作来表现这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产物。诗,不仅仅是作家用文字符号写下的“语言的文本”,也是他们生命之泉流淌出的“心灵的文本”,诗人的精神产品,是他们心灵的阳光在文本中的照射和辉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文学的抒情特质,重文体的表达功能,重视文辞的美学特点,重视表现技巧的丰富完善。“绮縠纷披,宫徴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把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辞采及声律的美都概括进来了,这是“文学自觉”的全面性的成就。尤其是永明之际,对诗歌语言的美有了飞跃性的认识,几乎把汉语的内在美都发掘了出来:如何运用汉语声调的清浊抑扬,构成诗文中错综和谐的声韵,使之富于乐感;如何运用对偶,使单音节的汉语具有连贯而又错落的节奏感;如何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使之或者华艳或者雅正;如何组织运用语言,使之含有言外之意。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的总趋势是朝着重诗歌的艺术特质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重抒情,重形式美的探求,重表现手段和表现方法。从东汉开始,这种变化已经出现迹象,扬(雄)、张(衡)、崔(骃)、蔡(邕)等人,清辞丽句,时发乎篇。汉末强烈抒情的诗──《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为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吹响了前奏曲。至于建安,“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建安诗人追求浓烈感情和风骨,也追求与风情融合无间的华美文辞。到了晋代,“潘(岳)、陆(机)特秀……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开始了对“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诗歌形式美的追求。南朝伊始,山水方滋,诗歌创作“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时的诗人对山水的美产生了如醉如痴的向往,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崇高潇散明秀、高雅脱俗之美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更加深入、全面地探求诗的形式美,有意识地讲求对仗,讲求修辞技巧,讲求用事用典,并注意到诗的声律问题。到了永明时代,诗歌变迁最显著的标志是声律说的出现。《南史·陆厥传》指出:
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章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徴不同,不可增减。
由此可见当时讲求声律的情形。前面已经述及,魏晋以降,诗向着美的方向发展,浓烈的抒情,词采的修饰,骈丽与用典,均已齐备。进一步的变迁与发展,必然要落到声律之美上来。永明年代以沈约为领袖的诗人群体,完成了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这一最后阶段的使命。对此,他有一段颇含自豪感的话语: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节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论》
从文学思想上看,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包含了抒情、风骨、辞采、骈丽、事典、声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从诗歌题材上看,唐诗中的各个题材种类,此时诗歌中均已涵盖;从诗人主体上看,他们的文学自觉意识,他们的文学与非文学(“文”与“笔”)意识都已完全具备,他们对诗的艺术美的追求也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经过这个时期的孕育,中国诗歌发展的巅峰──唐诗的出现,已为期不远了。
〔共八页〕
1
2
3
4
5
6
7
8
第一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