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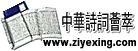 |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 |
|
文/朱光宝 海阔中文网网站整理收录·仅供参考
上编·诗体流变
第二章 乐府璀璨
第一节 文人乐府
两汉乐府诗歌的兴盛,在《诗经》《楚辞》之后,既开创了诗坛的新局面,又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就不会有汉末曹操诸人“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建安风骨”与“五言腾踊”的创作局面也不会出现;进而言之,也不会有北朝乐府的质朴之风和南朝乐府的绮艳之唱……换言之,乐府对建安及之后各体诗歌发展影响巨大。因而考察汉以后乐府之流变,极具价值。
汉乐府为浑朴天成的“歌诗”,魏晋以降,渐成二水分流:一是出现了大量的文人拟古乐府;二是有源源不断的乐府新歌问世,在六朝蔚为流行。
汉魏之交,大一统政权土崩瓦解,致使儒术衰颓而法术兴起。晋代傅玄感慨地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天下贱守节。”采诗观风的机制因此宣告式微。曹氏父子开始主盟文坛,宣告了文人拟古乐府时代的来临,乐府由民间文学向文人拟作过渡。
实际上,东汉文人即曾染指乐府创作,如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蔡邕《饮马长城窟行》等,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东汉文人诗歌精华《古诗十九首》,其中的《冉冉孤生竹》,《乐府诗集》即定为古辞;《驱车上东门》,《乐府诗集》作《驱车上东门行》。所以清代朱乾在《乐府正义》中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与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也都肯定这些诗是文人模仿学习汉乐府的产物。
建安时代,开始出现文人大规模创作乐府诗的壮观局面。从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诗歌的情况来看,曹操存诗全部为乐府歌辞,曹丕、曹植半数为乐府,曹叡则全为乐府。另外,《乐府诗集》收王粲乐府七首,阮瑀三首,繁钦一首。建安诗人吸收继承汉乐府一些成熟的艺术成果,又大力开拓崭新的艺术形态。
曹操的乐府诗遒劲刚健、悲凉慷慨,语言朴素,反映了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表现了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统一天下的大志。其《薤露》《蒿里行》就是这类题材的典范之作。《薤露》中以古题写时事。写董卓之乱:“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写迁都长安的惨相时说:“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写诗人对乱离的感受:“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行》叙述汉末群雄讨伐董卓时争权夺利,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的丧乱之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两篇乐府均属《相和歌·相和曲》,都是出殡时挽柩人唱的挽歌。《薤露》的古辞,言人命短促,像薤叶上的露水一样易于消逝。《蒿里》古辞记叙人死之后魂归蒿里的传言。同为挽歌,但又有分别,《薤露》是王公贵人出殡时所用,《蒿里》是士大夫庶人出殡用的。曹操的《薤露》以哀君为主,《蒿里行》完全是哀臣民所用,似乎也有等级之分。但从乐府流变来看,曹操开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风气。
王粲为建安七子之一,其古题乐府《七哀》,表现战乱中百姓流离转徙的凄惨景象。其第一首写他十六岁那年从长安逃难荆州途中所见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这类作品,悯乱哀时,震撼人心。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以及曹植的《泰山梁甫行》都是这类。
陈思王曹植《白马篇》《名都篇》《美女篇》不仅在体制上自出新题,而且在五言形式的发展上功不可没。其《名都篇》以首句开头二字名篇,摆脱了乐府旧题的约束,开唐代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先河。曹植描写叙述,剪裁细致,简略分明。清人吴淇《六朝选传定论》中有言:“凡人作名都诗,必搜求名都一切物事,杂错以炫博;而子建只单单推出一少年作个标子,以例其余。……于名都中,只出得一少年;于少年中,只出得两件事:一曰驰骋,一曰饮宴。”《美女篇》运用我国古代诗歌的传统手法,通篇用比,以美女不嫁,比喻志士怀才不遇,委婉而含蓄,“《美女篇》,意致幽渺,含蓄隽永,音韵节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使人不可仿佛端倪,固是空千古绝作……”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48页。曹植前期诗歌名作《白马篇》,文风骨气奇高,讲究用辞赡丽,语句工整,摆脱了前期乐府诗质朴的风格。
建安诗人的乐府诗,尽管不时露出“歌诗”的痕迹。但诗人的气质、政治使命,与时世动乱的交互作用,使他们的作品情调高昂、感情炽热充沛,化为慷慨悲凉的心曲,从而使乐府诗的风格为之一变。
首先,建安诗人增强了乐府诗的抒情成分。明徐祯卿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徐祯卿《谈艺录》,见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第769页。曹氏父子在关注外部世界的同时,开始更多地指向内在的主体心境,把自我的情志体验多侧面地表现在乐府诗中。方东树云:“曹氏父子皆用乐府题目自作诗耳。”黄节注,叶菊生校定《曹子建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2页。生逢乱世而怀用世之心,所以他们的乐府诗章时作自况之笔,读来尤觉“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曹操诗《短歌行》《龟虽寿》《秋胡行四解》等,均有时不我待的自励之意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魄。曹植的《白马篇》,朱乾评价为:“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黄节注,叶菊生校定《曹子建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70页。陈祚明曰《浮萍篇》:“应是自记思念之怀,故慨然于年命之不俟也”,又说《门有万里客》:“徙封奔走,或是自况,或他王亦然。”黄节注,叶菊生校定《曹子建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0页。这类的评价,不遑多举。
其次,建安诗人开始创作乐府徒诗。建安乐府诗入乐者为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著录的“三祖”乐府诗凡入乐的都有标明:或注明分“解”,或指明该诗曾为魏乐、魏晋乐、晋乐所奏。但曹植的近四十篇乐府,只有《怨诗行》一首(七解)、《野田黄雀行》(四解)、《怨歌行》四诗注明为晋乐所奏,其余不曾入乐。这些作品大多不再拘泥于古题古义。《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指出曹植拟《长歌行》为《鰕》;拟《苦寒行》为《吁嗟》;又云拟《豫章行》为《穷达》;拟《善哉行》为《日苦短》;改《泰山梁甫行》为《八方》。曹植为建安诗坛最杰出的诗人,其乐府诗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晋宋间陆机、鲍照等诗坛名家均直接取法于他,大开拟古乐府之风。
建安诗人得汉乐府浑朴自然之神髓,不仅赢得了“建安风骨”的美誉,且有“汉魏风骨”之并称。
晋宋时期,拟古乐府与乐府新歌此消彼长,交替发展。拟古乐府在西晋年间一度较为兴盛,出现了傅玄、张华、陆机等几位大家。他们所存乐府诗分别有:傅玄三十余首、张华十首、陆机四十八首。西晋文人乐府在体制上大抵模仿汉魏,而在文章结构方面略有一些创新。张华的《轻薄篇》在内容上保留了汉乐府关心现实的精神,而在形式上堆砌辞藻、繁缛乏味。傅玄《青青河边草篇》拟乐府古题《饮马长城窟行》而作,在结构上显得比原作更紧凑,描写抒情比原作细致,原作写梦很概括,人物心理也不如本篇写得深入。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远离原乐府诗的朴素,不惜在形式上铺陈,显著反映了魏晋诗歌从民间风格进一步转向文人风格的变化。
东晋百余年间萧条沉寂,找不到一个成气候的乐府作家。直到晋宋之际谢灵运、鲍照等人步入文坛后,才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谢、鲍所存乐府诗分别为十七首与八十六首),重新树立了乐府诗的地位。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晋宋诗人们或耽于安逸,系心玄理,或高蹈田园,寄情山水,缺乏摹写世态人情的创作动力与兴趣,除鲍照能够较好地继承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外,其他几家大多机械模仿古题古意,把拟古乐府的创作引入了歧途,其成就显然下建安诗人远甚。
晋宋诗人除模仿汉乐府外,亦兼酌前代乐府名家的艺术成果。陆机《鞠歌行·序》曰:“……又东阿王诗‘连骑击壤’,或谓蹙鞠乎?三言七言,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494页。东阿王指曹植,可见陆机对曹植的诗(包括乐府诗)相当熟悉并有所取法。陆机的《鞠歌行》主要采用“三言七言”的形式,而《乐府诗集》所收谢灵运、谢惠连的同题之作也是三言七言体,二谢当不愧陆机的异代“知己”。鲍照的《代陈思王白马篇》《代陈平原君子有所思行》诸作,也明确在诗题中表明了其师法对象。可以看出拟古乐府在一代代诗坛大家手中相传的轨迹。
齐梁陈三朝,文人乐府复兴,呈现出又一个高潮,涌现了一批批以宫廷为中心,以帝王贵族为代表的乐府作家群。他们留下的乐府数量远远超越了此前各朝,如王融四十二首,谢脁三十三首,梁武帝萧衍五十四首,沈约五十首,吴均三十八首,萧统七首,梁简文帝萧纲八十八首,梁元帝萧绎二十一首,张正见四十四首,陈后主六十六首,徐陵十九首,江总三十三首。六朝诗人本来存诗不多,因而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显示出此期文人乐府的兴盛。
齐梁帝王贵族日益习于偏安逸乐,既无汉武采诗以观民风的魄力,更无魏武“天下归心”的雄心壮志。礼乐衰微积重难返,加之陆机倡“诗缘情而绮靡”于前,简文帝主张“文章且须放荡”于后,导致宫体诗风泛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宫廷乐府背离了汉乐府的写实精神,寄托无有,风骨不存。宫廷诗人要么亦步亦趋模拟汉乐府古辞或名家之作,要么就乐府古题作空洞发挥,此唱彼和,蔚然成风,惜乎篇什虽多,却乏善可陈。
不过,在将乐府诗体推陈出新上,南朝宫廷诗人作出了一定贡献。随着旧乐陵替,新乐代兴,晋人所奏的汉魏旧辞,已有按合乐需要而宰割成以五七言四句为一解的。晋末以来的江南杂曲,也同样以五言四句体为主要形式。这种短小轻灵的体式自然成了齐梁君臣乐于模仿的对象。此外,他们还开始尝试七言四句体的模拟与创作,如《乐府诗集》所收梁武帝、沈约、简文帝《江南卉》十四首,简文帝、元帝、萧子显《乌栖曲》十一首,均为七言四句体。同时齐梁之际兴起的声律理论,也开始被谢脁、王融等人运用于古乐府及新乐歌的创作,产生了大量的“永明体”乐府。陈隋之际,徐陵、萧悫、庾信等人已有部分乐府诗具备了唐律的基本特征。这些诗体探索的成就,为唐代乐府形成“俱备诸体”打下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在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基础上,多借乐府诗抒情言志,在题材方面有所拓展,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对战争、边塞题材的开拓,对人生的感叹,对爱情的歌咏,对声色的追求等等,使乐府更加丰富多彩,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新的时代精神。
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在篇幅上变得日益繁复。如《乐府诗集·相和歌》中《箜篌引》只有四句:“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公堕河死(也作堕河而死),当奈公何!”但曹植的《箜篌引》不但内容与原题毫不相干,而且篇幅已达二十四句。
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形式自由多样。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在艺术方面有很大的变化。首先,语言由朴素转趋华美,在魏晋诗歌中有所体现,齐梁时期尤为盛行。如鲍照的《拟行路难》第二首:“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斫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承君清夜之欢娱,列置帏里明烛前。外发龙鳞之丹彩,内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异,对此长叹终百年。”作者极尽铺陈,用华美的字句描述龙鳞般美丽的金炉,麝香般沁人心脾的芬芳。其次表现手法也由以前的单调转为多样化。如曹植《美女篇》中“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明写桑树,暗写美女采桑的优美动作,“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通过写美女高贵的门第和美丽的容颜,隐喻诗人自己的身份和才能,比喻手法运用恰到好处。语言华丽、精练,同时通篇用比喻,以绝代美女比喻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以美女不嫁比喻志士的怀才不遇。含蓄委婉,意味深长。再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也是运用修辞巧妙的一篇佳作。全诗从放马于长城下山石间开始,借马说人,衬托出役夫难以忍受边地之苦,多由人物对话组成,句式也别具一格,文人一般只写四言、五言或者七言,而作者此诗运用长短句。乐府《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语句朴素自然。而鲍照的《代东门行》一首,开头“伤禽恶弦惊”就使用典故比喻“倦客恶离声”──游子最厌恶最害怕的便是离别之歌,从白天写到晚上,将行役之苦写得历历在目,下面突然插入两个比喻──吃梅总觉得酸,穿着葛麻布衣总是难以御寒,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即使宾朋满座,丝竹之声盈耳都无法排遣心中的忧伤,灵活运用比喻手法,自然贴切。
虽然魏乐府多以个人为主,题材较单调,晋乐府拟古而缺乏新意,南朝崇尚色情乐府,北朝乐府作者及作品寥寥,但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丰富了一代文学之体裁,在前至两汉,后至隋、唐的文人乐府创作中起了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这一时期中的声律之学的发达、四声八病的讲求,为隋唐之际的五、七言近体诗的奠基铺平了道路,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乐府新歌
六朝文学的另一个亮点是浑朴天然、清新活泼的乐府民歌,尤其是南朝以儿女私情为主的“吴歌西曲”。这是汉之后乐府的第二种流变。
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录情况,南朝乐府新歌大部分产生在东晋(近三百首),一部分产生在刘宋(一百五十余首),一部分署“晋宋齐辞”(一百二十余首),齐梁极少。这与《宋书·乐志》的记载相吻合:“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其后列举的《凤将雏歌》《前溪歌》《阿子》《闻欢歌》《团扇歌》《督护歌》《懊侬歌》《六变》《长史变》《读曲歌》等流行的曲调,绝大部分创制于东晋,仅个别创制于刘宋。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549-550页。
晋宋乐府新歌大量产生,有其社会原因。西晋“八王之乱”招致匈奴和羯族首领刘曜、石勒等大肆屠杀汉人,晋怀帝司马炽永嘉四年(310)刘曜大肆进攻内地,次年焚烧洛阳,中原官民大量南逃,史称“永嘉南渡”。其后偏居一隅的东晋延续百余年。420年,刘宋代晋。此后南方历经宋、齐、梁、陈四朝,共一百六十九年,没有大的战乱,经济得到了发展,民间歌舞也有较大的发展。《宋书·良吏传序》记载说:“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之极盛也。”《南齐书·良政传序》则云:“永明(齐武帝年号)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
南朝经济发达,带来文艺繁荣。统治者在绮幕珠帘、笙歌鼓乐的氛围中采集乐府民歌,有三个特点:一是女性情爱。这些民歌大都出自歌伎或商妇之口,且多以女子口吻来抒情或叙事。典范之作为长篇歌曲《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
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
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
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这种女性口吻的歌辞多写儿女私情,情调朴素,晋、宋以后流入宫廷,为帝王贵族所模拟,变成了南朝宫廷的艳情文学,素朴之风便不复存在。
二是市民情趣。南朝乐府的主要内容是“吴声”和“西曲”。“吴声”产地是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建业为六朝之都,秦淮河两岸歌楼楚馆云集。而“西曲”产于以长江中上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其中,竟陵(今公安)、襄阳、寿阳、江陵等地,都是当时长江中上游的商埠,市民的生活情趣,在这些歌辞中都有反映。
三是娱神祀鬼。民间祀神的《神弦歌》也是南朝乐府的突出内容。《古今乐录》称:“《神仙歌》十一曲,一曰《宿阿》,二曰《道君》,三曰《圣郎》,四曰《娇女》,五曰《白石郎》,六曰《清溪小姑》,七曰《湖就姑》,八曰《姑恩》,九曰《采菱童》,十曰《明下童》,十一曰《童生》。”所祀之神,不能尽考,多为各地的“杂鬼”。
北朝也有不少民歌产生,并输入南朝。如《乐府诗集》所收梁“横吹曲辞”六十六首。这些歌辞创作时间大概在梁以前,部分作品涉及的人物也有史为证。如《慕容垂歌辞三首》中的慕容垂系后燕开国君主,东晋太元九年(384)建国;《琅琊王歌辞八首》中的琅琊王系姚兴之子姚弼,姚兴曾仕前秦苻坚。北朝乐府“杂歌愿辞”《陇上歌》所歌颂的陈安,也是东晋时代人,《乐府诗集》引《晋书·载记》记载了他的事情。可见大部分北朝乐府应产生在晋宋时期,不晚于江南杂曲。
与汉乐府偏重叙事,内容深广不同,南北朝乐府民歌以抒情为主,多为五言短章(北朝乐府有少量四言体),体制向小型化发展。以轻灵之体,状单一情事,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过,在质朴天然的民歌本色上与汉乐府一脉相承。
齐梁以来,有众多的乐府歌诗集与古乐府集得以整理,使乐府诗影响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乐府》篇紧随《明诗》篇后步履单行,标志着乐府体系统理论的形成。魏晋六朝乐府泽被后人的,既有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也有日益完备的表现形式;既有建安诗人与鲍照师心自用的成功经验,也有晋代至梁陈宫廷诗人食古不化的反面教训。在此基础之上,以转益多师见长的唐代诗人才得以把乐府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共八页〕
1
2
3
4
5
6
7
8
上一页 下一页
|